《宠儿》_读书笔记2400字
一位英语点评老师推荐的书籍,
作者的文字功底儿很深!
不过可能原版会更好些,
书中有一部分没有标点符号。
黑尔、塞丝、丹芙、西克索、保罗…
他们不像是人,更像是动物,虽然有人的属性,但却没有人的待遇…
塞丝爱她的女儿,但却不愿意让她的女儿像她一样受苦、受辱~
所以她选择了杀死她的女儿~
他们的世界:
������黑尔的女人。年年怀孕,包括她坐在炉火旁告诉他她要逃走的那一年。
������渴望的一年,强奸似乎成了生活唯一的馈赠。他们使克制成为可能,仅仅因为他们是“甜蜜之家”的男人——当其他农庄主对这个说法警觉地摇头时,加纳先生吹嘘的那几个人。
������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在作第二次尝试。
������我永远不会再放她走了。尽管那毫无必要,我还是会向她解释的。我当时为什么那样做。就算我没杀了她她也会死的,可我不能容忍那样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
������我想方设法把奶水喂给她,甚至在他们抢走之后还给了她;在他们像对奶牛一样摆弄我之后,不,像对山羊,就在马厩背后,因为嫌我恶心,不能让我和马待在一起。
������所有贝比·萨格斯认识的人,更不用提爱过的了,只要没有跑掉或吊死,就得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
������她们到达的时候,塞丝已经体无完肤,只有包头发的布没被碰坏。她血淋淋的膝盖以下根本没有知觉;她的乳房成了两个插满缝衣针的软垫。
������所有死的东西活过来时都会疼的。
������一点米,一点豆,
就是不给肉。
干重活,累断腿,
面包没油水。
������他四年前去过罗彻斯特,在那儿看见五个女人,带着十四个女孩从别处来。她们所有的男人——兄弟、叔伯、父亲、丈夫、儿子——都一个一个又一个地被枪杀了。她们拿着一张纸片到德沃尔街的一个牧师那里去。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四五年了,可是白人黑人似乎都不晓得
������她孤身一人,而且腹中还怀着个让她牵肠挂肚的婴儿。她身后也许有狗,也许有枪;当然,肯定有生了青苔的牙齿。在夜里她倒不那么害怕,因为夜色就是她的肤色,可是到了白天,每一个动静都可能是一声枪响,或者一个追捕者悄悄接近的脚步声。
������巴迪先生的手也特别黑。你瞪他一眼就会挨鞭子。肯定会。我有一回瞪了他,他就大叫大嚷,还朝我扔火钳子。
������由于奴隶生活“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她什么都不剩了,只能靠心灵谋生——于是她立即付诸实践。她拒绝接受加在名字前的任何荣誉称号,只允许人们在名字后缀上一点东西以示爱戴[插图],就这样她成为一位不入教的牧师,走上讲坛,把她伟大的心灵向那些需要的人们敞开
������这个世界上除了白人没有别的不幸。
������解放自我是一回事;赢得那个解放了的自我的所有权却是另一回事。
������“学校老师”的侄子们玩弄她,而“学校老师”在一旁用她亲手制作的墨水记录下来;一
������到一个你想爱什么就爱什么的地方去——欲望无须得到批准——总而言之,那就是自由。
������要么是爱,要么不是。不浓的爱根本就不是爱。
������关于《逃犯法案》、“和解费”、“上帝之道”和黑人在教堂席位的真正含义的争论;不再有反奴隶制、解放奴隶、肤色选举、共和党人、德雷德·斯科特[插图]、读书、旅居者的高轮轻便马车、俄亥俄州特拉华县的黑人妇女联合会,以及其他把他们钉在椅子上,让他们两脚磨蹭地板,或者让他们痛苦不堪或兴奋异常地踱来踱去的重大问题。不再有对《北极星》或各种奇闻怪事的热切期待。不再有对一次新的背叛的喟然叹息,不再有对一次小小胜利的拍手称快。
������“你说的是哪个世界?凡间没有什么无害的东西。”
“有。蓝色。它不伤害任何人。黄色也是。”
������到了一八七四年,白人依然无法无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仅在肯塔基,一年里就有八十七人被私刑处死;四所黑人学校被焚毁;成人像孩子一样挨打;孩子像成人一样挨打;黑人妇女被轮奸;财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断。他闻得见人皮味,人皮和热血的气味。人皮是一回事,可人血在私刑的火焰里煎熬完全是另一回事。恶臭弥漫着。从《北极星》的纸页上弥漫而出,从证人的嘴里弥漫而出,在亲手递交的信件歪歪扭扭的字迹中铭刻着。恶臭在那些印满“有鉴于”、并呈递给所有相关法律机构传阅的文件和请愿书里得到详述,它弥漫着。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累坏他的骨髓。
������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的人。
������奴隶不应该有自己的享乐;他们的身体不应该是那样的,不过他们必须尽量多地生孩子,来取悦他们的主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许有内心深处的快乐。她对我说别听那一套。她说我应该永远听从我的身体,而且爱它。
������保罗·D听见男人们在谈话,头一回知道了自己的价格。他从来都是清楚、或者说相信自己清楚自己的价值的——作为一个人手,一个能给农庄赚钱的劳动力——可现在他得知了他的价格,就是说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标价。他的体重、力量、心脏、大脑、阴茎和未来的货币值。
������就告诉我这一件事。一个黑鬼到底该受多少罪?告诉我。多少?”
“能受多少受多少,”斯坦普·沛德说,“能受多少受多少。”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白人尽可以玷污她,却别想玷污她最宝贵的东西,她的美丽而神奇的、最宝贵的东西——她最干净的部分。那段带着记号挂在树上、无头无脚的躯干,是她的丈夫,还是保罗·A;爱国者们在黑人学校放的那场大火里,烧伤的姑娘中是否包括她的女儿;是否有一伙白人,侵犯了她女儿的私处,弄脏了她女儿的大腿,又把她女儿扔下大车:这些无法忍受的噩梦,她再也不要做下去了。她可以被迫在屠宰场的院子里干事儿,可她的女儿绝对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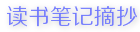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