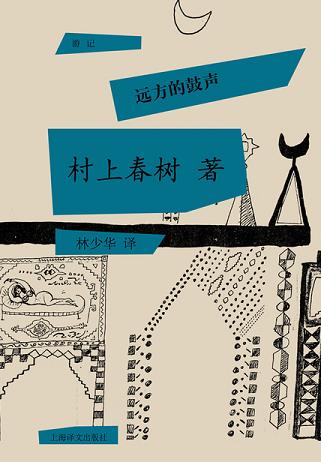
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时,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逃往了意大利。
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身居要职。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白天忙于政务,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
他有朴素的直觉: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抛弃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从城市到农村,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写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
村上春树和歌德都在37岁逃离了原来的轨迹,在更大的轨道里寻求更有内涵的自己,把三年旅欧见闻在《远方的鼓声》娓娓道来,当年欧洲的体制的陈旧捉摸不定的天气让他生厌,却让他一生挂念,让他写出了最富盛名的《挪威的森林》。我坚信这三年在欧洲的生活如同跑步一样彻底地影响了村上春树先生。
看完全书后,让我燃起了自己都害怕的愿望,在适当的时候我也要独自流浪一年,两年......直到觉得该回家的那一天。
远方的鼓声读书笔记及摘抄 第(2)篇看完之后又看了意大利电影《我去哪儿》,对意大利这种国民性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整部书到最后说的其实是迅哥“到异地,寻别样的人”,然后“苍蝇”似的回到原点的一种苦闷。身为异乡人的压抑与自由相伴相生,那样环境下写出来的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冷战即将终尾的时刻,被二战战败豁免掉战争权益的日本国民,有一种超然的“局外人”之感。疏离吗?倒是异常地亲切与体贴,于个体生活的细节中体贴入微,于苦行的工作和身体锻炼中寻求现实的慰藉。果然是新世纪美学的预言者。那张烈日下孤独跑着马拉松的“愤青”形象回应着历史的遗留物。然后也要“以物喜”“以己悲”地走向“自然”吗?在时代的潮流里随波逐流,漠然置之,顽石一样让海浪冲来皱纹、苔藓和虾蟹吗?悲愤其中,无由摆脱。
远方的鼓声读书笔记及摘抄 第(3)篇村上先生的游记,书名一般都比较敷衍,尤其是欧洲的纪行往往直接用地名了事。《远方的鼓声》一看名字还是很吸引我。看完觉得和其它游记比起来,语言风格还是保留了村上式的犀利与幽默,但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明显,碎碎念式的抱怨充斥其中。而且完全没有时间逻辑,地点也不停的穿梭与意大利和希腊,弄得我神魂颠倒。在我看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突然理解这就是一个长期处在自己喜欢的城市的人对这个的城市的不完美才不能容忍的抱怨。大概是比别人更爱吧。
不知道如今的意大利是否有了改观,毕竟三十年过去了,我魂牵梦萦的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锡耶纳,甚至西西里岛,都没有老去。但愿在我和你们相见时,不再是村上先生记忆里的冷漠混乱,和小偷多如牛毛……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