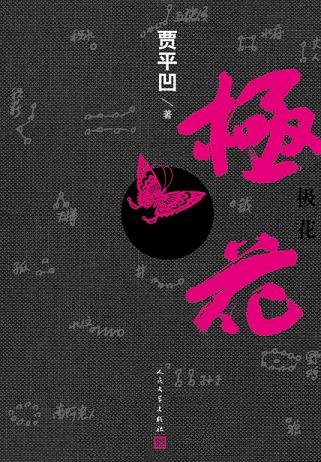
看完一声叹息。
看到一半以后还是觉得很好看,按照我的想法,蝴蝶可能会爱上黑亮,被解救出去,会因为割舍不下对老公和孩子的爱而又返回那个极度贫穷、落后、愚昧的地方。没想到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看了贾平凹的后记,知道这个小说是有所控诉,有所意义的。我觉得好的小说不一定非要控诉什么,有什么社会意义或时代意义,小说只要好看、精彩就足够了。其实,最算被解救的蝴蝶不被周边的人指点、评头论足,被家人被弟弟接纳而充分理解她,她就会重新开始新生活,忘记那个有自己亲生孩子的地方吗?不会的,女人只要有了孩子,全世界就都是孩子,何况小说后部分已经写出蝴蝶对黑亮是有爱的。
黑亮很爱蝴蝶,迁就了快一年,才在他爹的安排和那些光棍的怂恿下强迫和蝴蝶同房,平日里家人都吃土豆,他会开拖拉机老远给蝴蝶买馒头,买羊肉,家里的几只鸡相继都给蝴蝶炖汤了。看到这些我觉得读者也会喜欢黑亮和他爹吧。如果黑亮一家虐待蝴蝶,她还会那么眷顾孩子而割舍不下吗?
也许回去,黑亮以后再走出来,对蝴蝶来说未必不是好事。蝴蝶被拐卖是极度不幸的,让所有人同情,但遇到黑亮,蝴蝶又是幸运的,他不是糟老头,不是残疾人,没有家庭暴力,一家人都非常善良,还经营着一家小卖店,黑亮和他爹都很疼爱蝴蝶,这也许就是好多读者对贾平凹控诉的原因吧,确实作者让读者理解了受害人,但直接施害者是人贩子啊!
人生不到最后谁知道自己会有多少不幸,人贩子才是这个世界最该死的人,法律应该对人贩子严惩,否则,拐卖会一直存在。
极花 读书笔记 第(2)篇贾老以很轻松笔法去写胡蝶的不幸遭遇,这样就赋予主人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应对自己当前的处境。贾没有去以自己的怨恶来引导读者的情绪,更多的是让你自己去字里行间体会与回味,所以读起来轻松自在不压抑。这样的风格同样也在他之前的作品《高兴》中体现。读余华的《活着》也有这种感觉。好的作品不用作者刻意去引导读者的好恶,文字的魅力其义自见。
《极花》名字取得极好,冬虫夏草,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有些反季节,这就预示着胡蝶终究会是个有别于它的结局。
人与人之间,相处长了会日久生情 。更何况胡蝶已经生下自己的骨肉。难以割舍的血脉,难以割舍的亲情。她如果不回去,才是她人性的缺憾。
农村人虽然说些糙理糙话,但究其本质还是质朴。黑亮一家对待胡蝶就犹如如获至宝,左右邻居对她也尊敬有加,相处亲切和睦。反观胡蝶回到城里,除了媒体对所长的大肆宣扬就是对她人格的轻蔑与侮辱。口水的力量几乎要将其淹没。
母亲,她心心念念的母亲,迫于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要将她远嫁他乡。这又何尝不让人理解为是另一种形势的“拐卖”呢?而区别仅仅在于亲人的同意或是不同意。如若胡蝶隐忍远嫁,后果又会是何样一种悲剧呢?谁又是真正的从胡蝶的角度考虑过呢?就连自己的亲弟弟都没能被勾起同情,又何尝能得到别的外人的尊重?
所以,胡蝶最终选择了回归山村,因为她就是一朵极花,她的星星就在那儿的天空上,她真正属于那里,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
极花 读书笔记 第(3)篇看这种乡土小说,恍惚间觉得是姥爷在用方言极为动听地给我讲故事,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终于找到我喜欢这种类型小说的根源。
在我小时候,姥爷家是窑洞,盘有炕,姥爷很有讲故事的本事,睡前故事一个接一个,我却激动不已再也不想乖乖去睡,会问“接着呢?”,要么就是“再讲一个吧”,直到姥爷打起呼噜,我才罢休。回到家我的故事瘾还没过,还会缠着爷爷给我讲,爷爷比姥爷有文化却不会讲故事,听了一遍就不想再去听了。
这就是环境致使我成了我吧,以前受一个学姐影响去读严歌苓,但越来越觉得觉得她的文字太纠缠,很多描述我得反复地去看,看明白了也觉得无多大意思,相比起来我更喜欢直白明了不加修饰的描述。学姐她更细腻一点,我想要更粗犷袒露些。不一样才有意思,不是吗?
回到这部小说吧,真人真事改编,被拐卖的胡蝶被解救出来却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认了命。如今社会大转型时期,生出许多畸形怪诞的现象,作者笔下仅是普通一例。繁华之地无以立脚却还要拼死挤进去,物欲泛滥成了艺术,贫瘠之地广袤无垠却只剩老弱病残,基本的欲求实用性得不到满足。虽不能以偏概全,但也却是绝大多数,苏东坡是在少数人之列,在后记中作者提到“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不幸,而他的所有文字里竟没有一句激愤和尖刻。他是超越了苦难、逃避、辩护,领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真谛而大自在着。”做人当作苏东坡呀!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