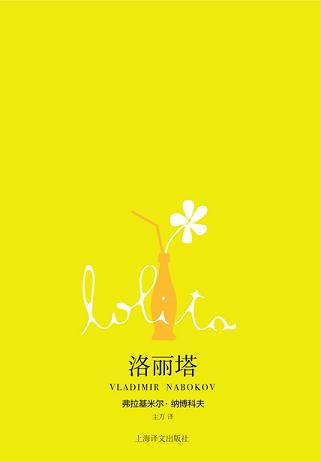
初读是在好几年前,那时候电子书资源稀缺,二手书也抬到天价,我为了找到于晓丹译本的《洛丽塔》费了好大一番劲。主万译的这本确实如蒋方舟所说——作者时时刻刻在提醒读者这是一份证词,言下之意是——这是不可信的。但这个译本更大的问题是翻译事故造成的歪歪扭扭的假象,不知这个和所谓道德上的粉饰和欺骗哪个更可恶。相比这份证词,几年前阅读过的于晓丹译本则更像一个梦境,除了情节,回忆起来尽是扑簌簌的蝴蝶和挥拍时的风,过量的形容词被破折号和遥远的括弧搭救,虽然坎坷但也算颤颤巍巍地到达犯罪现场。另外,非常著名的开头“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出现在于晓丹译本里,在这个译本里不是这么翻的。《洛丽塔》是我阅读经历里的一个魇,不仅仅因为它让我开始畏惧文学里的谎言,一些大词像炮弹虚伪又坚硬的外壳——爱与罪,美与道德——破裂后雷霆万钧于表达者的耳膜。亨伯特杀奎尔蒂是自毁的方式吗?亨伯特是爱洛丽塔还是仅仅是欲望的困兽?洛丽塔对奎尔蒂的激情是与亨伯特有关的吗?这些问题困扰我很多年,再读多少遍也不会有答案,或者说纳博科夫讥笑当头,我不敢有答案。好一点的说法应该是“我知道这有罪,但我也知道这是爱”,作者让亨伯特犯了一个被美化过的罪行,踩到了一些非常极致的痛脚,以至让这本书的存在也变成了罪孽。《洛丽塔》是一个整体艺术(这样高密度的语言闭环下一个只能在《爱达》里找到,《爱达》其实更好,无论是文学语言内部还是社会反响所谓外部都像一个实心球,密不透风又严丝合缝地探讨一些美不胜收又恬不知耻的议题)。这不是承认自己是包法利夫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黑塞和昆德拉的“原型”问题(恋童和乱伦的结合可能只在纳博科夫那里是一个被二次三番使用的母题),甚至不是一个讨论文该不该载道的问题,这是文学究竟能不能创造出虚假的真实的问题(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追溯到一个“真实故事”,很奇怪,我们竟然有从这样的一个说法里寻找满足的病态的癖好。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知作家也和我们自己一样没聪明到能自己编造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更加看得起自己了呢?或者,当我们得知在我们不可思议地瞧不起的“虚构”下面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我们可怜的想象就增添了几分力量了呢?或者,概括起来说,这里是否体现了我们对于事情的真实性的崇拜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小孩子们会问讲故事的人:“真有这样的事吗?”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老托尔斯泰在过于追求道德伦理的时期止步不前,不敢亵渎神明,像上帝创造人类一样,去创作完全虚构的人。是否如此?)。虽然这个译本冷静异常,但纳博科夫的颜料还是渗透了语言——“长命百岁,我的情人”,没有哪种阅读能这样,把人读得像大病一场。
洛丽塔 读后感 第(2)篇看完整部小说,不觉美好n洛丽塔天真坦率、叛逆冷漠,但又不是完全没心没肺,她了解她继父对她的爱恋,但不能苛责一个处于性萌芽又恰遇叛逆期的孩子如何搞清状况,于是她半推半就的,半强迫半享受地浸在这种关系中,无知地任由其发展。所以洛丽塔和亨伯特之间的感情谈不上相爱,只是亨伯特的一厢情愿和洛丽塔的无知叛逆造就了这段主流看来“扭曲”的感情。在亨伯特的自述中我没有看出任何美感,在描述亨伯特对洛丽塔的迷恋时,语气带着神经质的狂热,而在他想对洛丽塔图谋不轨的时候,这种的占有欲更谈不上让人舒适。有读者提到这是“中年男人的劫数”,我不太理解,这和男人喜欢青春活力的小女生是不一样的,亨伯特产生如此异于常人的举动,更多的是初恋女友十四岁离去后给他造成的心里阴影的映射,所以才对“性感少女”有种狂热的执念,而恰好,同为“性感少女”的洛丽塔又有着令他着迷的性格特质,所以对她格外长情而已。本以为这本书就这样浅浅淡淡看下去,没有叹息,可是看到最后还是被亨伯特的剖白触动。他对洛丽塔说:“务必忠实于你的狄克。不要让别的家伙碰你。不要跟陌生人谈话。我希望你会爱你的孩子。我希望他是个男孩。我希望你的那个丈夫会永远待你好,否则,我的鬼魂就会去找他算账,会像黑烟,会像一个疯狂的巨人,把他撕成碎片。不要可怜克·奎。上帝必须在他和亨·亨之间作出选择,上帝让亨·亨至少多活上两三个月,好让他使你活在后代人们的心里。”n但这仍不足让人惋惜n爱是克制,既然放纵了自己,就别求成全。
洛丽塔 读后感 第(3)篇一本关于恋童癖的爱情宣言。未看书之前,只知大概是一对年龄差较大的两人故事,看了以后发现,大概不只是年龄差了。亨伯特因为自己的心理畸形对洛丽塔一见钟情,但却因为世俗而与其母结婚,之后仍对洛丽塔不死心,确切的说,是对有着少女姿态的性感妖娆怀有不道德的欲望。单从这个故事来说,不道德太不道德了,恋童癖在现实生活中是很不齿的心理畸形,即便后来亨伯特对洛丽塔有着确确实实的爱意,也不能抵消他对洛丽塔做出的伤害。一个可以还说是儿童的女孩,在懵懂无知的时期与一个父辈年龄的人发生了关系,自此童年这样度过,进而早熟,最终在整个人生里都有一段卑微不忍回首的记忆。但是从文字方面来说,纳博科夫写的真的太棒了,曾听人说他擅长反讽模仿甚至是游戏性的态度。单就洛丽塔来说,纳博科夫将他的文字运用的登峰造极。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容许各种互相对立的读者层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一个每位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不同含义、不同特色、甚至不同故事的潘多拉的盒子。——略撒n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