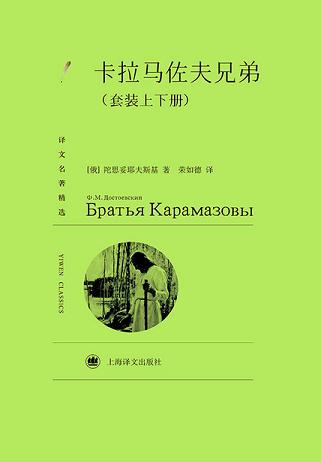
一 、为什么要读陀老
据说,李安写剧本,想突出某个人很有思想很有内涵,就给他一个特写,让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说陀老是深刻的代名词,我想是无可争议的。
但深刻也有深刻的弊病。
譬如我们说某一个人的作品很深刻,那他的作品一般是不易读的,不轻松的,至少不是消费层级的。陀老的作品确实如此。
读陀老时,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我为什么要读陀老?
是生活太轻松了吗?读点爽点的不好吗?
是为了装?显摆下,摆个Pose,读陀老!人生在世,不要逢场作戏。
是实用吗?我们知道时下最流行的读物,一种叫鸡汤,一种叫鸡血。鸡血可以让人热血沸腾,激情四射;鸡汤可以给你短暂快感,聊以慰藉。鸡汤鸡血更实用。
事实上,鸡血和鸡汤是组合拳。打完一剂鸡汤后,头脑发热;发现改变不了生活的时候,来一煲鸡汤降降温,生活又美滋滋。那格格不入的深刻有什么用?
《圆桌派》的作家们也想讨论这个问题。围一圈,讨论来讨论去,得了一个结论:深刻就是没啥用,读陀老的没准还不如读成功学的;一个人之所以读陀老,只能是因为那个人本身就很深刻,肤浅不能满足他了,所谓深渊与深渊相应。
换句话说,读陀老的原因是:人就是喜欢读陀老,你管的着吗?
这个解释很好,但我认为似乎还有更好的解释。
直到近期,我听了郭暮云先生的一个推送,突然恍然大悟。
深刻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经典范式。
这是什么意思了?每个人脑海里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自己头脑中文本的映射。这种说法当然不能等同于文本即世界,但可以说文本解读世界。
你脑中的范式,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
譬如,我们听到“你是风儿,我是沙。”第一反应也许不是大漠的豪情,而是缠绵悱恻的爱情。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眼见”被你头脑中的经典范式解读了。
多读情爱小说,你也许观察世界更多浪漫主义;多读武侠类,你对社会的解读可能不自觉快意恩仇、狭义江湖;同理,你多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能洞悉更多的人性,更加认识自己。
你读的每本书都不同程度地储存在你的头脑里,在你脑中留些范式,构建体系帮助你解读你所看到的世界。
那么问题来了,你愿意储存些畅销读物,还是储存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了?
我想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会不会读陀老。
二 、陀老行文的一些特色
为什么读陀老说了很多,再谈谈陀老的文字。
我有慕名读过陀老一些作品,对陀老的写作手法和行文风格略微了解。
我只分享三个点。
1.简单来讲,就是不拘一格,再说白点就是粗糙。
木心评论陀老的粗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他不会营造很大的场景,很戏剧的情节,因为陀似乎把全部心力用在挖掘更深的人性。
平常生活,字字句句,皆是精彩,皆是好戏。
因为舞台之上,正是赤裸的人心。
2.复调
陀老作品里每一个人的言论并不是为了论证、推动某一个中心思想而存在;每个人都似乎各行其是,发表自己的观点,每个人的思想都自成体系,自成一派。
陀老并不是第一个使用复调的作家,但他却将复调推到极致。
你经常会看到一个中心向前推进,突然被一个路人“不识趣”地带偏题,跑到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熟悉这种风格后,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风景。
3.宗教
陀老是目前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这句话唯一的争议只在于,这句话最后是否需要加上“之一”。
不同于神学家,陀的神学体系必须且只能以小说的方式来表达,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因为别的方式,你说不清楚。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给你讲个故事,你明白了会心一笑,Get到了,惊叹他的智慧;你不明白,怎么说你还是不会明白。
以上三点在《罪与罚》中已经显露得非常成熟,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更是淋漓尽致。
三 、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些想法
说了半天,终归是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想法区,那就回归正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体情节其实非常简单。
老卡拉马佐夫一生糜烂,有四个儿子,米嘉、伊万、阿辽沙、半子(名字太长,我就叫他半子了,没有名分的儿子)。有一天,老卡拉马佐夫死了,那么凶手是谁?
陀老把整本书放在这样一个侦探小说的构架下,内容却包罗万象。
抽丝剥茧展开的不是案情,却是人心。每一页翻开都有惊喜,你窥探人心,云雾缭绕,你知道其中有大山,却看不清它的来龙去脉。
我素来有阅读即时写想法的喜欢,唯独此书,所写无几。因为实在不知道每个人物、每个故事的脉络和走向,不敢妄论。只到故事结束,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人心真是最大的奥秘。
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米嘉的爱情线,一条阿辽沙的探索线。老实说,两条线交织并不紧密。
有专业人士甚至认为米嘉是艺术的极致,处处高光,而阿辽沙那条线都是臃肿的冷调宗教伦理,毫无兴致。
那位人士指出,阿辽沙线的卡西马长老,大男孩,小男孩如果尽数删掉,丝毫不影响文本主体构成,文本结构甚至会更聚焦和完整。
他所言可能正确,失去阿辽沙,文本结构可能完美;但失去阿辽沙、卡西马、大小男孩,宗教的灵魂就失丧了。
整个文本的骨正是救赎与复活,以及支撑这个体系的论述。也可以说,阿辽沙、卡西马正是陀老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具体内容太多,不便多说。
佐西马长老这样一个经典人物,不像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塑造的主教,只有言行与教义。陀老为这位长老塑造了支撑他言行与教义的“重生见证”,使得这位长老有血有肉;他的教导就是他的生命。在我看来,佐西马长老和他所代表的基督精神正是文本的灵魂。
其中不少章节耐人寻味。譬如宗教大法官、伊万和魔鬼的对话、法庭对弈,甚至单独成篇都称得上经典,高潮迭起。字数有限,我也不做妄评了。
读这本书时,我一直有一个担忧,很害怕看完后无书可读。就像一个书友说的,自己总有种偏见,俄罗斯那几部作品一读,其他经典都跟畅销书无异了。
大抵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
希望以后能遇到更好的书,如若不能,一辈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我的幸运。
实在是字数受限,书评并未展开。如果有机会,我下次书评会就内容具体分享。
最后,引纪德的话: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以上。
卡拉马佐夫兄弟(套装上下册)(译文名著精选)读后感500字 第(2)篇这不是一本能有良好阅读体验的书,大段大段的对话和心理活动,冗长,啰嗦,且行文粗砺,更可怕的是,书中主要人物除了阿辽沙和佐西玛长老,其他都或多或少显得莫名其妙甚至是神经质,很难理解这些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机制,到了后面伊万居然精神分裂,和自己另一个人格直接对话。唯一支撑我读下去的是书中的悬疑氛围和强大的情感渲染力。
如果仅仅将本书看做简单的二元对立,理性和信仰的相克,善与恶的斗争,现代科学文明和古老宗教精神的较量,那也没什么错。但作者所写的卡拉马卓夫兄弟是有三个人,代表欲望的大哥卡嘉,代表理性的二哥伊万,代表信仰的三弟阿辽沙。有趣的是,这三个人中,阿辽沙最通透,最纯粹,但也最没个性,少有欲望和理性的一面,而大哥卡嘉既有欲望的冲动,也有真诚的信仰。二哥伊万则是最复杂、最黑暗、最纠结的形象,他信仰,但又怀疑自己的信仰,他有理性,可又抗拒这种理性,他同样也有欲望,只不过相比大哥的冲动而言,他的欲望更隐蔽。这三兄弟中我最喜欢的也是伊万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处于信仰奔溃年代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科学发展起来后西方文明的缩影。
也许伊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过的困惑,但阿辽沙才是他的寄托。实际上这本书还没写完,作为本书的主人公,阿辽沙还会去体验更多的经历,去考验自己的信仰。不过书没写完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情节上或许本书是有所缺失的,但在思想上这本书却是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这本书中展现了自己毕生的思考。至于阿辽沙最终会如何,其实并不难预料,他极有可能就是下一个佐西玛长老,问题是能不能走得更远,而我倒是希望他能多一些个性。
没有宗教基础的人挺难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对于阿辽沙的寄托,在我看来不过是无谓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早就预料到上帝必死的结局。不要想,只要信,可是怎么可能不想呢?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像佐西玛长老那样超凡的智慧,还真的不要去想,倒不如做一只绵羊比较好。这就说到书中由伊万讲述的故事《宗教大法官》,这个故事其实可以从小说里独立出来,有关该故事的研究浩如烟海,这也是本书几个小故事里最深刻、最令人费解的一个。很难去反驳那个宗教大法官的言论,即便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没有宗教大法官这么极具煽动性的演说,而即便不考虑宗教因素,还能从中读出极权主义的威胁。
我很喜欢佐西玛长老讲他哥哥的那个回忆,相对于小说的情节,书中的小故事反而让我印象更深。一个狂妄自大的社会主义青年怎么就真心皈依宗教了?也许对于个人来说,想要实现自身的幸福,并不需要多少宗教的东西,但对于人类整体来说,要想实现全人类的幸福,某些宗教的东西必不可少,就像佐西玛长老的诘问,请问你们这些现代文明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精英,打算用什么来代替宗教,如果将彼岸撤除,那拿什么来作为全人类的尺度?又有哪一个尺度能像宗教那样深、那样博大、那样直抵灵魂?(非原文,大致意思)
“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是忏悔。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爱和希望。
卡拉马佐夫兄弟(套装上下册)(译文名著精选)读后感500字 第(3)篇用时38小时读完七十多万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一本大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集大成之作,相比之下《罪与罚》简单纯粹得多,但也一脉相承,如一个人的青年和中年。这本书读起来很累,像在负重前行。内容丰富,关于宗教和精神信仰,关于欲望和本能,关于嫉妒和虚荣,关于亲情和爱情,关于犯罪心理,关于善恶,关于社会,关于家庭,关于儿童,关于道德.律法制度,关于敬畏,关于上帝…七十多万字,人物不多,故事也不复杂,却被作者呈现地如此淋漓尽致、精彩纷呈,匆匆阅读一遍,也仅仅是吸收了少部分养分,需要一读再读。对老陀作品的喜爱和佩服已经不能用文字来表达,但读完也疲惫不堪。老陀的书有毒,有分量,绪言中译者对本书的评价是启卷和掩卷之时已判若两人。这个分界在哪里?很难说清楚,就像善恶、美丑这些两极化的概念,我只知道它们在我心里越来越接近,黑白分明的绝对观念何尝不是建立在明显的偏见和强权之上的呢?n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