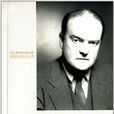
纽约知识分子丛书:埃德蒙·威尔逊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是美国20世纪广受尊崇的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家。近半个世纪里,他以真挚的人文情怀、冷静独立的思考和晓畅明晰的语言,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以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视野,为千万读者呈现了20世纪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历史画卷。这位文化巨擘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如《阿克瑟尔的城堡》、《光明的彼岸》、《创伤与神弓》、《三重思想家》、《到芬兰车站》等,至今影响深远。他的逝去,代表着美国一个文化时代的终结。 本书考察了威尔逊对欧美文学所做出的经典批评,显示出威尔逊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超越;同时也从威尔逊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出发,向读者展示他的文化关注。从传统的特权阶层走出来的这位老派文人,在参与历史的过程中书写历史,在评介文学的过程中总结文明。他不断行走在文学和现实之间,“他的历史观使他的手记变成了社会文献,他的回忆录转变为文化历史,他的评论变成了文学编年史”。
基本介绍
- 书名:纽约知识分子丛书:埃德蒙·威尔逊
- 作者:邵珊ˆ季海宏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544740548
- 外文名:Edmund Wilson
-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 页数:225页
- 开本:32
- 品牌:江苏译林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美国最后一个文学通才”埃德蒙·威尔逊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和社会批评家,影响直至今天。放在现今的视野里,他的文学批评中的注重审美性和人文主义精神,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履行和人文关怀,依旧可以照进现实。作为文学批评家,他竭力发掘、提携新人,梳理美国文学脉络;他反对学院派的那一套闭门造车、闭关自守的作风,提倡跨学科的研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突破局域,走向公共生活,批判新英格兰文雅传统、格林尼治村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走出美国30年代左派的激进转向人文主义的回归,关注美国原着民等边缘文化群体,思考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他展现了美国半个世纪的文化全景和文明样态,,在参与历史的过程中书写历史,在评介文学的过程中总结文明。“他的历史观使他的手记变成了社会文献,他的回忆录转变为文化历史,他的评论变成了文学编年史”。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展现了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一生,整本书偏记叙不偏学术,还有一些对威尔逊婚姻、与纳博科夫文学论战等轶事的爆料。
他展现了美国半个世纪的文化全景和文明样态,,在参与历史的过程中书写历史,在评介文学的过程中总结文明。“他的历史观使他的手记变成了社会文献,他的回忆录转变为文化历史,他的评论变成了文学编年史”。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展现了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一生,整本书偏记叙不偏学术,还有一些对威尔逊婚姻、与纳博科夫文学论战等轶事的爆料。
作者简介
邵珊
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範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系交流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文化和英语教育。先后在《外国文学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季海宏
比较文学博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为南京师範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副所长,剑桥大学BEC考试南京考官队队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语言教学和符号学。
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範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系交流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文化和英语教育。先后在《外国文学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季海宏
比较文学博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为南京师範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副所长,剑桥大学BEC考试南京考官队队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语言教学和符号学。
专业推荐
媒体推荐
如果美国文明存在的话,是威尔逊先生把它展现给我们,而他自己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时代周刊》
名人推荐
埃德蒙·威尔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良心。——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威尔逊无穷的生命力和他对文学的狂热之爱是他作为一个评论家长盛不衰的原因。——哈罗德·布鲁姆
埃德蒙·威尔逊是20世纪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有个性魅力并着迷于生活的人。——小亚瑟·施莱辛格
“有了他清晰的解析,我们才有了探索二十世纪文学的导航图。”——珍妮特· 格洛斯
威尔逊无穷的生命力和他对文学的狂热之爱是他作为一个评论家长盛不衰的原因。——哈罗德·布鲁姆
埃德蒙·威尔逊是20世纪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有个性魅力并着迷于生活的人。——小亚瑟·施莱辛格
“有了他清晰的解析,我们才有了探索二十世纪文学的导航图。”——珍妮特· 格洛斯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威尔逊的人文主义批评观
1.人文批评之旅的起点与终点
2.共和梦想的伤与痛
3.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承
3.1.罗尔夫和高斯
3.2.泰纳和阿诺德
3.3 前辈门肯
4.批评家职责的再定义
5.批评的非功利性态度
5.1.“创伤”与“神弓”密不可分
5.2.“神弓”≠“工具”
6.文学批评的文学性
7.多维度的社会历史批评
第二章 威尔逊与欧美文学
1.狄更斯不为人知的痛苦
2.菲茨杰拉德成功的背后
3.海明威唯一尊重的批评家
4.平民化的《尤利西斯》
4.1.象徵主义——现代情感叙事途径
4.2.平民话的《尤利西斯》
4.3.城堡内外
5.是小说还是批评?
6.文学的历史叙述
6.1.欧陆传统与本土创新
6.2.独立文学身份的创建
7.历史的文学叙述
8.与纳博科夫的争执
8.1.从交流到争执
8.2.势不两立的开始——《洛丽塔》
8.3.分道扬镳——关于《奥涅金》译文的争论
8.4.最后的争端
第三章 公共知识分子威尔逊
1.也说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2.威尔逊的公共立场
3.在主流文明的边缘
4.在历史的深处
5.威尔逊的“大政治”
6.威尔逊与学院派
结语
注 释
参考书目
主要人名英汉对照表
埃德蒙·威尔逊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第一章 威尔逊的人文主义批评观
1.人文批评之旅的起点与终点
2.共和梦想的伤与痛
3.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承
3.1.罗尔夫和高斯
3.2.泰纳和阿诺德
3.3 前辈门肯
4.批评家职责的再定义
5.批评的非功利性态度
5.1.“创伤”与“神弓”密不可分
5.2.“神弓”≠“工具”
6.文学批评的文学性
7.多维度的社会历史批评
第二章 威尔逊与欧美文学
1.狄更斯不为人知的痛苦
2.菲茨杰拉德成功的背后
3.海明威唯一尊重的批评家
4.平民化的《尤利西斯》
4.1.象徵主义——现代情感叙事途径
4.2.平民话的《尤利西斯》
4.3.城堡内外
5.是小说还是批评?
6.文学的历史叙述
6.1.欧陆传统与本土创新
6.2.独立文学身份的创建
7.历史的文学叙述
8.与纳博科夫的争执
8.1.从交流到争执
8.2.势不两立的开始——《洛丽塔》
8.3.分道扬镳——关于《奥涅金》译文的争论
8.4.最后的争端
第三章 公共知识分子威尔逊
1.也说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2.威尔逊的公共立场
3.在主流文明的边缘
4.在历史的深处
5.威尔逊的“大政治”
6.威尔逊与学院派
结语
注 释
参考书目
主要人名英汉对照表
埃德蒙·威尔逊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后记
从初识威尔逊,开始构思,到今天这此书的出版,前后历经了十年的时间。
十年,可以发生许多事情,产生诸多变化。
这十年中,关于“后理论时代”文学批评走向的讨论不绝于耳: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然后呢?下一个文学批评或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好像关于文学批评向何处去的讨论从来就没有休止。作为一名讲授英美文学的大学老师,自己也被带到了这个插满路标的十字路口,在新理论产生的新鲜感逐渐消退之后,又不免生出颇多困惑。和威尔逊的邂逅使我从这种嘈杂和困惑中一点一点地解脱出来。有时候,看看这些老派的批评家,内心就会觉得淡定许多。
十年前,是我的导师钱满素教授介绍我“认识”了威尔逊。通过十年间和老师的交往,随着自己研究的不断深入,我逐渐明白她推荐我们研究威尔逊、特里林、卡津等文化大家的深意。读威尔逊越多,越是发现导师与这些老派文人治学风範的神似之处。老师不光学问做得扎实,更有春风化雨般的个人魅力。记得在某个书店的门匾上看到这样一句话:“读书是最美丽的姿态。”钱老师虽已年愈花甲,但我看到的依然是她的美丽。她一生都在读书,都在写作,因此,岁月留给她的不是容颜已逝的伤感和遗憾,而是不经意间流露的从容和娴静,这样的美丽是一种力量和影响。
十年间,我所在学院的院长张杰教授一直对这套书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的今天,张老师是我所见过的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锲而不捨,殚精竭虑,他的治学和为人带动着我们,使我们和理想越来越近。
在这十年里,我的先生和我一起收集、整理、研读资料,一起完成了这本小书,一起慢慢地变老。
十年时间,我的女儿已从家中的“小丸子”出落成和我比肩的花季少女,她见证了我读书和写书的艰辛,记得她六岁时说她不想长大,因为长大了还得写威尔逊,这样让人忍俊不禁的言语一定是因为看到妈妈的辛苦,听到妈妈的抱怨。现在懂事的她会调侃地安慰我,如果这本书有销量的话,那就是她买下的那一本。
十年可以磨一剑,但我自知本人才疏学浅,能力有限,磨出的是不是剑没有把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十年的确磨砺了我的性格,使我更加踏实,更爱读书。
邵珊
2013年5月于南京
十年,可以发生许多事情,产生诸多变化。
这十年中,关于“后理论时代”文学批评走向的讨论不绝于耳: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然后呢?下一个文学批评或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好像关于文学批评向何处去的讨论从来就没有休止。作为一名讲授英美文学的大学老师,自己也被带到了这个插满路标的十字路口,在新理论产生的新鲜感逐渐消退之后,又不免生出颇多困惑。和威尔逊的邂逅使我从这种嘈杂和困惑中一点一点地解脱出来。有时候,看看这些老派的批评家,内心就会觉得淡定许多。
十年前,是我的导师钱满素教授介绍我“认识”了威尔逊。通过十年间和老师的交往,随着自己研究的不断深入,我逐渐明白她推荐我们研究威尔逊、特里林、卡津等文化大家的深意。读威尔逊越多,越是发现导师与这些老派文人治学风範的神似之处。老师不光学问做得扎实,更有春风化雨般的个人魅力。记得在某个书店的门匾上看到这样一句话:“读书是最美丽的姿态。”钱老师虽已年愈花甲,但我看到的依然是她的美丽。她一生都在读书,都在写作,因此,岁月留给她的不是容颜已逝的伤感和遗憾,而是不经意间流露的从容和娴静,这样的美丽是一种力量和影响。
十年间,我所在学院的院长张杰教授一直对这套书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的今天,张老师是我所见过的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锲而不捨,殚精竭虑,他的治学和为人带动着我们,使我们和理想越来越近。
在这十年里,我的先生和我一起收集、整理、研读资料,一起完成了这本小书,一起慢慢地变老。
十年时间,我的女儿已从家中的“小丸子”出落成和我比肩的花季少女,她见证了我读书和写书的艰辛,记得她六岁时说她不想长大,因为长大了还得写威尔逊,这样让人忍俊不禁的言语一定是因为看到妈妈的辛苦,听到妈妈的抱怨。现在懂事的她会调侃地安慰我,如果这本书有销量的话,那就是她买下的那一本。
十年可以磨一剑,但我自知本人才疏学浅,能力有限,磨出的是不是剑没有把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十年的确磨砺了我的性格,使我更加踏实,更爱读书。
邵珊
2013年5月于南京
序言
前 言
一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是20世纪美国极为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不仅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历史广度丰富和拓展了整个美国文艺批评领域,而且还以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情怀关注着美国文化的流变。简单地说,威尔逊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对社会现实的诗性把握。威尔逊首先是个文学评论家,但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评论家。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他不仅关注到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批评家本身的艺术素养,还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特性和人文关怀。正是这种诗性把握和人文关怀使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超越了文学,从更为巨观的角度看,他的文学批评展现的是对美国文明发展的全景画卷。
威尔逊1895 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名为红斑克的小镇,家族有着深厚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背景。1912年他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威尔逊不再囿于他所熟悉的社会圈子和生活方式,让他亲历了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複杂。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在《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和《纽约书评》等着名杂誌主持文学和文化批评专栏并担任评论主笔。这些杂誌成为他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前沿阵地。随着批评羽翼的丰满,威尔逊的涉猎面也不断地拓宽,他渐渐地以文学记者身份步入到美国文化的核心地带。他一生给后人留下的多种文集、随笔、日誌等都是他梳理美国文明脉络的努力,为我们的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威尔逊一生着述颇丰,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后渐入佳境,并逐步达到巅峰。他曾对狄更斯、萧伯纳和简·奥斯丁等主流作家做出过经典批评,还提挈并介绍过许多当时不被公众所关注的非主流作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就是在他的积极鼓励和鼎立相助下走上了美国文坛的前沿,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显赫的作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其文学批评成名作《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像文学研究》中,威尔逊以清晰晓畅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马塞尔·普鲁斯特、T·S·艾略特 、詹姆斯·乔伊斯等现代文学大师的风采,第一次把《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等旷世佳作引入美国公众的视野和讨论之中。威尔逊不仅以其极具前瞻性的慧眼使美国文坛意识到这些现代作家的重要性,而且也大大缩小了高雅文学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
从他20年代的早期小说创作《想念戴茜》起,威尔逊就明确地对外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艺术家应该走出小圈子,去拥抱更博大丰富的生活;他在30年代的两部重要的文学评论集《创伤与神弓:文学论文七篇》和《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就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前者强调的是批评家如何在艺术家和公众之间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使艺术服务于生活;后者则以生动的“城堡”意象来隐喻艺术家脱离生活就是对创造力和艺术生命力的扼杀;在40年代的历史巨着《到芬兰车站:历史的写作和行动之研究》中,他将这个主题发挥到了极至,他用列宁来到圣彼得堡芬兰车站领导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抱负和使命的象徵。对列宁形象的再塑造生动诠释了威尔逊对知识分子身份和职责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仅传承了18世纪人文主义精神——即人类一切学识和思想都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生活都应该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目标;而且也呼应了美国文化精神的奠基人爱默生在其随笔《美国学者》中对知识分子意义和职责的界定。爱默生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思想着的人,但他的思想不能被传统和书本所束缚,他应该还是一个行动的人。所谓“行动”就是要继承和传播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思想,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思想。知识分子是“世界的眼睛”。他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全人类,而不是仅仅传达给其他少数的知识分子。诗人夏皮罗曾对威尔逊做出这样的评价:“威尔逊的评论成就在于他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图景结合为一,从抽象分析家手中盗取文学之火。他可能是现代评论家里唯一可以无私、博学而勤恳地把我们这一代的科学、社会、美学与创作灵感带回大众的注视之中的人。”
《三维思想家》是威尔逊30年代的另一部有影响的文学评论集。三维思想家这一概念是说,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里,仅有“艺术”这一维度是不够的,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多维度的,包括对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哲学、心理等多方面的关照。“三维思想家”这一名称不仅是威尔逊对艺术家的精神修养的要求,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作为文学评论家,威尔逊的文化批评,就像一面多稜镜,从多维度折射出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中,威尔逊一共写过20多部文化评论着作,这些论着以美学、社会和政治为主题,以散文、诗歌、剧本、游记和历史传记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抒发着他对美国文化各个层面的思考。这些文化批评始终同美国的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体现了惊人的历史跨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传统和价值观的重建,20年代“歌舞昇平”下掩盖的空虚和混乱,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的社会动荡和百姓的生活状态,从30年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40年代对存在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少数民族宗教和生活图景的描绘,到50年代在以色列发现的死海古卷对基督教起源的质疑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把威尔逊的这些批评集结在一起,我们将看到美国半个世纪的文化全景。美国文明是威尔逊一生的研究主题,反过来,他的一生也是我们研究美国文明的重要文本。正如《纽约时报》对威尔逊所做的评价:“如果有美国文明的话,是威尔逊先生帮助我们发现了它,而他本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威尔逊不仅为读者提供了高水準的文学赏析,他的文学批评本身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审美的享受。如舍曼·保罗对威尔逊所作的评价:“他的艺术的大部分就是他的批评,一个批评家的艺术就是要激发思想并解决思想的问题,而他最好的批评就是艺术。”威尔逊认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是不够的,批评家应首先是艺术家,是善于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的作家。因为只有具备了艺术家素质的批评家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他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而且,文学评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就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是观察人类意念与想像如何被环境模塑的一种历史。”所以,批评家不仅需要敏锐的历史意识和科学的研究能力,更需要丰富的想像力,是想像力赋予了文学批评艺术的感染力。除此之外,威尔逊对语言文字的热爱和驾驭使他的文章明晰、有趣、并具有鲜明的个性。威尔逊把“清晰、流畅和说服力”看作是文学评论写作的最高境界。威尔逊批评的艺术感染力使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他渗透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便得以向更广泛的公众辐射。
纵横美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被人们略带伤感地称作是“美国最后一个文学通才。”今天像威尔逊这样不仅具备专业素养,又有独立思想和现实情怀的文学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确实很难找了。在威尔逊批评生涯的后期,正值形式主义批评甚嚣尘上,在此之后结构、解构、后现代等主义纷纷大行其道。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学批评从一个大众化的文化活动,渐渐屈从了高度专业化社会的发展需要,开始在学院的围墙内生存。可以说,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不愿盲从和跟风的威尔逊是孤独的,而他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同时又为那些学院派所不齿,他们认为威尔逊不过是个高雅文学的“普及者”。
无论学术界如何变化,威尔逊始终坚持自己艺术判断和批评的独立性。有人形象地把威尔逊比作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战士。在知识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一个艺术家仍然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实在难能可贵,这样的独立和自由使他能够长久保持艺术家的想像力、敏锐尖利的批评锋芒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观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中叶,当威尔逊的文学批评和影响力在美国达到巅峰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文学批评还处在被政治占领的年代,那时的评论家们“完全失去了作为独立的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性,没有自己的思想、趣味和语言。”是一个“评论缺位的时代”。当时,受过严格外国语言文学训练的人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还是熟悉的,但这也仅限于对威尔逊文学範围之内的关注,对于他的人文关怀则不仅是学者们的盲点,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雷区。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内文学批评界开始进入较为自由和独立的状态,国外大量的学术思潮也随之进入中国。因此,在80年代国内文学批评界曾出现过一次“充满激情和想像”的高潮。当时的评论家们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他们随时準备着为启蒙大众,推动社会前进而献身。但是,各种思潮的涌动也使文学批评界呈现浮躁的心态,于是,进入90年代后,面对浮躁和鱼龙混杂,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冷静思考,主张知识分子应当返回学术界、重建学术规範。当时国外的文学批评也已经成为学院语境下的专业化批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开始退出公共的领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有自己的岗位,即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不再向社会提供现实意义。90年代后,儘管批评界围绕“专业研究”和“公共关怀”有过几次讨论,但后现代话语、学科专业化、以及以福柯为代表的特殊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知识现象。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以人文关怀,文化干预为批评目的的传统文学批评家威尔逊被边缘化了,甚至被质疑在当下的语境,研究威尔逊是否还有价值,因为他没有提出过鲜明的理论或体系。然而,我们知道,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一样是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民族的文化,维护人类的理性与良知。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批评家的声音。像威尔逊这样的“社会良知”的渐行渐远是一个时代的损失。80年代,由美国开始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把威尔逊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威尔逊的批评灵魂就是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显着特徵。在理论标新立异,术语推陈出新的文学批评气候下,我们重新研究威尔逊就是对人文传统的回归,就是回到文学的最本源。因为,威尔逊代表的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他是一个真正推广文学的人,他相信人文精神是文学批评之根本,是文学批评的生命。
二
美国学术界对威尔逊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一些知名学者如珍妮特· 格洛斯、舍曼·保罗以及刘易斯· M · 戴伯尼等都撰写了关于威尔逊研究的专着,他们从生平、文学创作、批评方法和影响等方面从不同的视角对威尔逊进行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刊杂誌和论文集中的文章也从不同侧面展现威尔逊的批评风采。
舍曼·保罗1965年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文学界研究》是一部较早期的威尔逊研究专着。该书以时间顺序追述了威尔逊生平中的几个重要阶段,从这些阶段的代表作品中揭示威尔逊思想发展和批评特色,以及威尔逊作为一个自由学者的人格魅力。1955年在美国文学艺术学会授予威尔逊罕见的随笔与批评金奖时,范·怀克·布鲁克斯称威尔逊是仅有的几个可以称得上是作家的批评家,他代表了“一种行将消失的类型,一个自由的文人。”这也正是保罗所要论证的威尔逊的人格。他的职业操守使他在乱世中仍能洁身自好,保持那种他所说的“天才的勇气”,对威尔逊而言,一个文人仅有天才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具备道德和才智上的勇气,只有这样,他的天才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正是这样的人格和精神才使威尔逊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有着比他同时代的文人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保罗的《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文学界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有着深刻文化意味的威尔逊传记,他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固然重要,但只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生命之树常青。
如果说保罗的研究注重的是威尔逊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人所具备的一种精神的话,珍妮特·格洛斯则是针对威尔逊批评方法的纯学术研究。格洛斯是威尔逊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之一,出版过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本《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批评家》中,格洛斯细读了威尔逊对叶芝、普洛斯特、詹姆斯和普希金等人的批评,并从中归纳出威尔逊的批评方法、批评目的以及批评风範。这部学术着作出版于80年代末,当时正是一个研究威尔逊的学术高潮,格洛斯的一些结论沿用至今,如她从威尔逊的批评精神和脉络中找到了法国历史批评家圣勃夫、泰纳以及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等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批评精神使得威尔逊能够超越文本,触及读者,关注生活。
怀俄明大学英语教授刘易斯·M ·戴伯尼2005年9月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人生》是迄今为止美国学界关于威尔逊研究最新和最全面的一本传记。该传记就是通过对威尔逊一生的深入挖掘来展示“他的传记就是文学史”这样的观点。
戴伯尼为该传记起的书名耐人寻味,尤其在读过这本传记后我们会有更深刻的感触:《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人生》,一个看似平常的题目,然而,读过这本书回头再细细品味才觉出它的巧妙。这个题目可以看作是包含着双重意思:首先,“文学人生”总结了威尔逊一生生活和文学的互动,文学为威尔逊的文化批评和指点人生提供了最佳的平台。而在他一生都不曾间断的文学评论中,他始终把艺术家看作是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个“主人公”,他要通过想像力再现他们的人生,从而还原他们所处的那段文化历史。
再者,书名“A Life in Literature”不仅概括了威尔逊的文学人生,而文学中的这个“life” 更是威尔逊文学批评的关键字。作为文学批评家,威尔逊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发掘和保留文学中的生命和生机,他远离理论和学院的一些做法和“偏见”,其实是害怕一些东西会伤及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元气。“埃德蒙·威尔逊批评家身份的长存归因于他无穷的生命力和对文学的强烈的热爱。这些特性在戴伯尼这本意味深长的传记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从这样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出传记人戴伯尼是深得威尔逊秘笈的,这样的题目对于诠释威尔逊的文学人生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威尔逊生前就有意让传记家戴伯尼为自己立传,他愿意有人能在他身后把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戴伯尼不负众望,这本厚重的传记为我们描摹了一个真实全面的威尔逊。书中追述了从爵士乐时代到甘迺迪当政这几十年中威尔逊思想和艺术的发展,描述了威尔逊怎样从一个小城镇的温雅绅士一步步走向美国文化舞台的中央,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最终以“最后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战士”而谢幕。
威尔逊个人的历史与美国文学的发展史是如此的环环相扣,他用自己真诚和犀利的批评应和着美国文学史上的每一次起伏。作为一本传记,戴伯尼不仅向我们呈现了威尔逊有声有色的文学人生,他还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少有局限,鲜有保留。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真实的威尔逊,他不仅是一个批评大师,一个美国文化现象的呈现者,他还有着常人所具有的各种怪癖和缺点,这些缺点使威尔逊更加的鲜活生动起来,如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对此书所做出的评价:“埃德蒙·威尔逊是20世纪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有个性魅力并着迷于生活的人。戴伯尼在传记中以深刻、谨慎和发人深省的叙述对威尔逊一生的各个方面给予了公正恰当的处理。”
上述这些专着都是威尔逊文学批评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充分表明了国外威尔逊研究已经具有的规模。然而,这样一个在欧美国家颇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至今国内尚未开始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进行系统的介绍和研究,这多少是一种缺憾,与威尔逊对美国及世界文学及文化所做的贡献以及所获的声名相比显得很不平衡。本书试图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而全面地将威尔逊研究引入中国的语境之中,抛砖引玉,引发国内学者对威尔逊的研究兴趣,让读者认识一位久未“谋面”的文人—— 一位能激发思想、针砭时政、引领审美品位和社会道德的文化大家。这是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做过,但又很值得一做的事。况且,威尔逊的批评理论和灵魂就蕴涵于他的为人为文中,他的文学观点一旦得到呈现和树立,其影响力自然就会发生。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单纯的威尔逊文学批评研究,而是给予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以相同的比重,并将他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目的既凸显了威尔逊的文学批评特色,又表现了他的批评活动超越文学批评本身,向文化和文明递进的中心主题。
一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是20世纪美国极为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不仅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历史广度丰富和拓展了整个美国文艺批评领域,而且还以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情怀关注着美国文化的流变。简单地说,威尔逊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对社会现实的诗性把握。威尔逊首先是个文学评论家,但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评论家。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他不仅关注到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批评家本身的艺术素养,还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特性和人文关怀。正是这种诗性把握和人文关怀使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超越了文学,从更为巨观的角度看,他的文学批评展现的是对美国文明发展的全景画卷。
威尔逊1895 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名为红斑克的小镇,家族有着深厚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背景。1912年他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威尔逊不再囿于他所熟悉的社会圈子和生活方式,让他亲历了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複杂。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在《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和《纽约书评》等着名杂誌主持文学和文化批评专栏并担任评论主笔。这些杂誌成为他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前沿阵地。随着批评羽翼的丰满,威尔逊的涉猎面也不断地拓宽,他渐渐地以文学记者身份步入到美国文化的核心地带。他一生给后人留下的多种文集、随笔、日誌等都是他梳理美国文明脉络的努力,为我们的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威尔逊一生着述颇丰,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后渐入佳境,并逐步达到巅峰。他曾对狄更斯、萧伯纳和简·奥斯丁等主流作家做出过经典批评,还提挈并介绍过许多当时不被公众所关注的非主流作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就是在他的积极鼓励和鼎立相助下走上了美国文坛的前沿,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显赫的作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其文学批评成名作《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像文学研究》中,威尔逊以清晰晓畅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马塞尔·普鲁斯特、T·S·艾略特 、詹姆斯·乔伊斯等现代文学大师的风采,第一次把《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等旷世佳作引入美国公众的视野和讨论之中。威尔逊不仅以其极具前瞻性的慧眼使美国文坛意识到这些现代作家的重要性,而且也大大缩小了高雅文学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
从他20年代的早期小说创作《想念戴茜》起,威尔逊就明确地对外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艺术家应该走出小圈子,去拥抱更博大丰富的生活;他在30年代的两部重要的文学评论集《创伤与神弓:文学论文七篇》和《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就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前者强调的是批评家如何在艺术家和公众之间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使艺术服务于生活;后者则以生动的“城堡”意象来隐喻艺术家脱离生活就是对创造力和艺术生命力的扼杀;在40年代的历史巨着《到芬兰车站:历史的写作和行动之研究》中,他将这个主题发挥到了极至,他用列宁来到圣彼得堡芬兰车站领导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抱负和使命的象徵。对列宁形象的再塑造生动诠释了威尔逊对知识分子身份和职责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仅传承了18世纪人文主义精神——即人类一切学识和思想都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生活都应该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目标;而且也呼应了美国文化精神的奠基人爱默生在其随笔《美国学者》中对知识分子意义和职责的界定。爱默生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思想着的人,但他的思想不能被传统和书本所束缚,他应该还是一个行动的人。所谓“行动”就是要继承和传播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思想,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思想。知识分子是“世界的眼睛”。他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全人类,而不是仅仅传达给其他少数的知识分子。诗人夏皮罗曾对威尔逊做出这样的评价:“威尔逊的评论成就在于他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图景结合为一,从抽象分析家手中盗取文学之火。他可能是现代评论家里唯一可以无私、博学而勤恳地把我们这一代的科学、社会、美学与创作灵感带回大众的注视之中的人。”
《三维思想家》是威尔逊30年代的另一部有影响的文学评论集。三维思想家这一概念是说,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里,仅有“艺术”这一维度是不够的,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多维度的,包括对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哲学、心理等多方面的关照。“三维思想家”这一名称不仅是威尔逊对艺术家的精神修养的要求,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作为文学评论家,威尔逊的文化批评,就像一面多稜镜,从多维度折射出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中,威尔逊一共写过20多部文化评论着作,这些论着以美学、社会和政治为主题,以散文、诗歌、剧本、游记和历史传记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抒发着他对美国文化各个层面的思考。这些文化批评始终同美国的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体现了惊人的历史跨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传统和价值观的重建,20年代“歌舞昇平”下掩盖的空虚和混乱,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的社会动荡和百姓的生活状态,从30年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40年代对存在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少数民族宗教和生活图景的描绘,到50年代在以色列发现的死海古卷对基督教起源的质疑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把威尔逊的这些批评集结在一起,我们将看到美国半个世纪的文化全景。美国文明是威尔逊一生的研究主题,反过来,他的一生也是我们研究美国文明的重要文本。正如《纽约时报》对威尔逊所做的评价:“如果有美国文明的话,是威尔逊先生帮助我们发现了它,而他本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威尔逊不仅为读者提供了高水準的文学赏析,他的文学批评本身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审美的享受。如舍曼·保罗对威尔逊所作的评价:“他的艺术的大部分就是他的批评,一个批评家的艺术就是要激发思想并解决思想的问题,而他最好的批评就是艺术。”威尔逊认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是不够的,批评家应首先是艺术家,是善于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的作家。因为只有具备了艺术家素质的批评家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他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而且,文学评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就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是观察人类意念与想像如何被环境模塑的一种历史。”所以,批评家不仅需要敏锐的历史意识和科学的研究能力,更需要丰富的想像力,是想像力赋予了文学批评艺术的感染力。除此之外,威尔逊对语言文字的热爱和驾驭使他的文章明晰、有趣、并具有鲜明的个性。威尔逊把“清晰、流畅和说服力”看作是文学评论写作的最高境界。威尔逊批评的艺术感染力使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他渗透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便得以向更广泛的公众辐射。
纵横美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被人们略带伤感地称作是“美国最后一个文学通才。”今天像威尔逊这样不仅具备专业素养,又有独立思想和现实情怀的文学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确实很难找了。在威尔逊批评生涯的后期,正值形式主义批评甚嚣尘上,在此之后结构、解构、后现代等主义纷纷大行其道。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学批评从一个大众化的文化活动,渐渐屈从了高度专业化社会的发展需要,开始在学院的围墙内生存。可以说,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不愿盲从和跟风的威尔逊是孤独的,而他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同时又为那些学院派所不齿,他们认为威尔逊不过是个高雅文学的“普及者”。
无论学术界如何变化,威尔逊始终坚持自己艺术判断和批评的独立性。有人形象地把威尔逊比作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战士。在知识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一个艺术家仍然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实在难能可贵,这样的独立和自由使他能够长久保持艺术家的想像力、敏锐尖利的批评锋芒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观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中叶,当威尔逊的文学批评和影响力在美国达到巅峰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文学批评还处在被政治占领的年代,那时的评论家们“完全失去了作为独立的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性,没有自己的思想、趣味和语言。”是一个“评论缺位的时代”。当时,受过严格外国语言文学训练的人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还是熟悉的,但这也仅限于对威尔逊文学範围之内的关注,对于他的人文关怀则不仅是学者们的盲点,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雷区。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内文学批评界开始进入较为自由和独立的状态,国外大量的学术思潮也随之进入中国。因此,在80年代国内文学批评界曾出现过一次“充满激情和想像”的高潮。当时的评论家们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他们随时準备着为启蒙大众,推动社会前进而献身。但是,各种思潮的涌动也使文学批评界呈现浮躁的心态,于是,进入90年代后,面对浮躁和鱼龙混杂,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冷静思考,主张知识分子应当返回学术界、重建学术规範。当时国外的文学批评也已经成为学院语境下的专业化批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开始退出公共的领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有自己的岗位,即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不再向社会提供现实意义。90年代后,儘管批评界围绕“专业研究”和“公共关怀”有过几次讨论,但后现代话语、学科专业化、以及以福柯为代表的特殊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知识现象。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以人文关怀,文化干预为批评目的的传统文学批评家威尔逊被边缘化了,甚至被质疑在当下的语境,研究威尔逊是否还有价值,因为他没有提出过鲜明的理论或体系。然而,我们知道,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一样是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民族的文化,维护人类的理性与良知。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批评家的声音。像威尔逊这样的“社会良知”的渐行渐远是一个时代的损失。80年代,由美国开始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把威尔逊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威尔逊的批评灵魂就是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显着特徵。在理论标新立异,术语推陈出新的文学批评气候下,我们重新研究威尔逊就是对人文传统的回归,就是回到文学的最本源。因为,威尔逊代表的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他是一个真正推广文学的人,他相信人文精神是文学批评之根本,是文学批评的生命。
二
美国学术界对威尔逊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一些知名学者如珍妮特· 格洛斯、舍曼·保罗以及刘易斯· M · 戴伯尼等都撰写了关于威尔逊研究的专着,他们从生平、文学创作、批评方法和影响等方面从不同的视角对威尔逊进行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刊杂誌和论文集中的文章也从不同侧面展现威尔逊的批评风采。
舍曼·保罗1965年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文学界研究》是一部较早期的威尔逊研究专着。该书以时间顺序追述了威尔逊生平中的几个重要阶段,从这些阶段的代表作品中揭示威尔逊思想发展和批评特色,以及威尔逊作为一个自由学者的人格魅力。1955年在美国文学艺术学会授予威尔逊罕见的随笔与批评金奖时,范·怀克·布鲁克斯称威尔逊是仅有的几个可以称得上是作家的批评家,他代表了“一种行将消失的类型,一个自由的文人。”这也正是保罗所要论证的威尔逊的人格。他的职业操守使他在乱世中仍能洁身自好,保持那种他所说的“天才的勇气”,对威尔逊而言,一个文人仅有天才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具备道德和才智上的勇气,只有这样,他的天才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正是这样的人格和精神才使威尔逊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有着比他同时代的文人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保罗的《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文学界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有着深刻文化意味的威尔逊传记,他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固然重要,但只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生命之树常青。
如果说保罗的研究注重的是威尔逊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人所具备的一种精神的话,珍妮特·格洛斯则是针对威尔逊批评方法的纯学术研究。格洛斯是威尔逊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之一,出版过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本《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批评家》中,格洛斯细读了威尔逊对叶芝、普洛斯特、詹姆斯和普希金等人的批评,并从中归纳出威尔逊的批评方法、批评目的以及批评风範。这部学术着作出版于80年代末,当时正是一个研究威尔逊的学术高潮,格洛斯的一些结论沿用至今,如她从威尔逊的批评精神和脉络中找到了法国历史批评家圣勃夫、泰纳以及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等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批评精神使得威尔逊能够超越文本,触及读者,关注生活。
怀俄明大学英语教授刘易斯·M ·戴伯尼2005年9月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人生》是迄今为止美国学界关于威尔逊研究最新和最全面的一本传记。该传记就是通过对威尔逊一生的深入挖掘来展示“他的传记就是文学史”这样的观点。
戴伯尼为该传记起的书名耐人寻味,尤其在读过这本传记后我们会有更深刻的感触:《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人生》,一个看似平常的题目,然而,读过这本书回头再细细品味才觉出它的巧妙。这个题目可以看作是包含着双重意思:首先,“文学人生”总结了威尔逊一生生活和文学的互动,文学为威尔逊的文化批评和指点人生提供了最佳的平台。而在他一生都不曾间断的文学评论中,他始终把艺术家看作是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个“主人公”,他要通过想像力再现他们的人生,从而还原他们所处的那段文化历史。
再者,书名“A Life in Literature”不仅概括了威尔逊的文学人生,而文学中的这个“life” 更是威尔逊文学批评的关键字。作为文学批评家,威尔逊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发掘和保留文学中的生命和生机,他远离理论和学院的一些做法和“偏见”,其实是害怕一些东西会伤及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元气。“埃德蒙·威尔逊批评家身份的长存归因于他无穷的生命力和对文学的强烈的热爱。这些特性在戴伯尼这本意味深长的传记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从这样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出传记人戴伯尼是深得威尔逊秘笈的,这样的题目对于诠释威尔逊的文学人生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威尔逊生前就有意让传记家戴伯尼为自己立传,他愿意有人能在他身后把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戴伯尼不负众望,这本厚重的传记为我们描摹了一个真实全面的威尔逊。书中追述了从爵士乐时代到甘迺迪当政这几十年中威尔逊思想和艺术的发展,描述了威尔逊怎样从一个小城镇的温雅绅士一步步走向美国文化舞台的中央,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最终以“最后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战士”而谢幕。
威尔逊个人的历史与美国文学的发展史是如此的环环相扣,他用自己真诚和犀利的批评应和着美国文学史上的每一次起伏。作为一本传记,戴伯尼不仅向我们呈现了威尔逊有声有色的文学人生,他还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少有局限,鲜有保留。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真实的威尔逊,他不仅是一个批评大师,一个美国文化现象的呈现者,他还有着常人所具有的各种怪癖和缺点,这些缺点使威尔逊更加的鲜活生动起来,如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对此书所做出的评价:“埃德蒙·威尔逊是20世纪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有个性魅力并着迷于生活的人。戴伯尼在传记中以深刻、谨慎和发人深省的叙述对威尔逊一生的各个方面给予了公正恰当的处理。”
上述这些专着都是威尔逊文学批评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充分表明了国外威尔逊研究已经具有的规模。然而,这样一个在欧美国家颇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至今国内尚未开始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进行系统的介绍和研究,这多少是一种缺憾,与威尔逊对美国及世界文学及文化所做的贡献以及所获的声名相比显得很不平衡。本书试图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而全面地将威尔逊研究引入中国的语境之中,抛砖引玉,引发国内学者对威尔逊的研究兴趣,让读者认识一位久未“谋面”的文人—— 一位能激发思想、针砭时政、引领审美品位和社会道德的文化大家。这是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做过,但又很值得一做的事。况且,威尔逊的批评理论和灵魂就蕴涵于他的为人为文中,他的文学观点一旦得到呈现和树立,其影响力自然就会发生。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单纯的威尔逊文学批评研究,而是给予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以相同的比重,并将他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目的既凸显了威尔逊的文学批评特色,又表现了他的批评活动超越文学批评本身,向文化和文明递进的中心主题。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