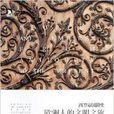
西方帝国简史:欧洲人的文明之旅
《西方帝国简史:欧洲人的文明之旅》是一本很简短的书,但主题却很庞大——大到可以直接称呼为世界历史。这是许多民族转变为庞大国家组织,即所谓的“帝国”的故事。历史学家帕戈登以精準且动人的笔法,讲述了远从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帝国的时代,直至欧洲殖民体系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崩解。帕格尔登迷人地连结起各殖民事业的因果关係,将它们的相似性与重要的不同之处抽丝剥茧地找出来,整理出它们命运的兴衰史。欧洲如何定义“新世界”?欧洲如何将奴隶制度结合在经济架构中,又得到了什幺结果?欧洲如何一次次找到新的理由,来证明他们支配其他民族是一个多幺慷慨和仁慈的行?帝国时代毕竟走向了终点,留下无法辨认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欧洲人以民族为起点建立帝国,再转变为国家,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帕戈登也为这样的问题留下了不少省思。
基本介绍
- 中文名:西方帝国简史:欧洲人的文明之旅
- 外文名:Peoples and Empire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 正文语种:中文
- 作者:安东尼•帕戈登 (Anthony P.)
-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 页数:224页
- 开本:16
- 包装:平装
- 译者:徐鹏博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212059231, 7212059234
作者简介
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先后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伦敦、巴塞隆纳、牛津等地接受教育。过去十八年间,他担任过剑桥大学的知识史高级讲师、国王大学的研究员,以及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他是霍普金斯大学布莱克研究中心的历史教授,并定期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纽约时报》撰稿。
帕戈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世界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外殖民地和非欧洲世界的关係。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他提出并运用“帝国”政治理论,具有启发性地分析了“西方”如何来解释自己怎样以及为什幺由它来主宰这个世界,并梳理了这种“西方治理”在世界範围内衰落的过程。
图书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首位世界征服者
亚历山大帝国是古代世界曾存在过的最辽阔的帝国,虽然它维持得并不长久,但仍然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世界,这些方式对欧洲所有民族随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简单地说,亚历山大统合了现今我们称为欧洲与亚洲的广大区域,也顺利统一了原本纷争不断且各自独立的希腊城邦。
第二章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为其居民提供了某种保护措施,一种我们称为“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好是坏),以及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伟大国度的成员资格。对贵族阶级而言,还提供了财富保护,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荣誉,而荣誉可以满足让他人尊敬且钦羡的欲望。
第三章 普世帝国
欧洲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是作为诸侯,运用自己的地位,来维持各个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这些势力包括:自由而隶属帝国的城镇、领主与公爵、诸侯、兼任君主的主教与不受约束的“自由帝国武士”——所有这些人都统治着日耳曼。以当时视为神圣的一句拉丁话来说,皇帝只能算是“相同地位中的第一人”。
第四章 征服海洋
在15世纪初期,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开始有点改变,1434年的一次远航虽然没有收穫,但证明了向着西非沿海能够往南走。到了17世纪,葡萄牙人已经能够到达从西非延伸到印度再到中国南部等地,那些大型商船每年都会载着大量财物返回欧洲。17世纪中叶,欧洲人已经有效地掌控大西洋,他们也是印度洋上最有势力的贸易商。
第五章 传播福音
这个全新的基督世界的秩序,此时它的起源并不能从罗马帝国的起源中分离,正如特土良曾经所说,这一秩序将与“俗世”共存。于是它将自己想像成不仅是人类的共同国度,而且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与道德秩序,也没有天然的边界。
第六章 伊比利亚世界的衰落
现在我们所说的“西班牙的衰落”,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叶就开始了。1568年,旧勃艮第公国的心脏地带尼德兰发生叛乱,随即蔓延到欧洲大部分国家,直到1648年西班牙最终被迫承认这个新国家的存在。
第七章 自由的帝国,贸易的帝国
一种全新的世界主义随之兴起。新教徒和资本主义北欧所形成的新兴帝国,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散布全球。不同的是,他们至少在名义上都是贸易帝国,儘量避免殖民和征服,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以财富而非军事的力量来发展。
第八章 奴隶制度
现代奴隶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与古代及中古时代相当不同。它开始于1444年8月8日的早晨,当时载有235名非洲人的第一批货船从今天的塞内加尔出发,在葡萄牙的拉哥斯港上岸。赞助航海事业的航海家亨利王子,从所有的奴隶中挑选出最好的五分之一,然后骑马离去,“黑金”贸易从此开始。
第九章 终极边疆
太平洋上的岛屿并不单是布乾维尔与康默森所描述的那般俗气逸乐,那里也是提供欧洲商船补给的地方,是前往传说中南方大陆的那条航线上的潜在据点。在西班牙的虎视眈眈之下,英法两国对南方海洋的潜在财富有着不确定但相当明显的计画。
第十章 帝国、种族、国家
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还是继续致力“教化野蛮人”。并藉此使世界各民族
结合为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总有一天,世界上被殖民的民族一定会“开化”。当那一天到来,他们必然要取回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结语
人物表
第一章 首位世界征服者
亚历山大帝国是古代世界曾存在过的最辽阔的帝国,虽然它维持得并不长久,但仍然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世界,这些方式对欧洲所有民族随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简单地说,亚历山大统合了现今我们称为欧洲与亚洲的广大区域,也顺利统一了原本纷争不断且各自独立的希腊城邦。
第二章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为其居民提供了某种保护措施,一种我们称为“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好是坏),以及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伟大国度的成员资格。对贵族阶级而言,还提供了财富保护,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荣誉,而荣誉可以满足让他人尊敬且钦羡的欲望。
第三章 普世帝国
欧洲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是作为诸侯,运用自己的地位,来维持各个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这些势力包括:自由而隶属帝国的城镇、领主与公爵、诸侯、兼任君主的主教与不受约束的“自由帝国武士”——所有这些人都统治着日耳曼。以当时视为神圣的一句拉丁话来说,皇帝只能算是“相同地位中的第一人”。
第四章 征服海洋
在15世纪初期,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开始有点改变,1434年的一次远航虽然没有收穫,但证明了向着西非沿海能够往南走。到了17世纪,葡萄牙人已经能够到达从西非延伸到印度再到中国南部等地,那些大型商船每年都会载着大量财物返回欧洲。17世纪中叶,欧洲人已经有效地掌控大西洋,他们也是印度洋上最有势力的贸易商。
第五章 传播福音
这个全新的基督世界的秩序,此时它的起源并不能从罗马帝国的起源中分离,正如特土良曾经所说,这一秩序将与“俗世”共存。于是它将自己想像成不仅是人类的共同国度,而且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与道德秩序,也没有天然的边界。
第六章 伊比利亚世界的衰落
现在我们所说的“西班牙的衰落”,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叶就开始了。1568年,旧勃艮第公国的心脏地带尼德兰发生叛乱,随即蔓延到欧洲大部分国家,直到1648年西班牙最终被迫承认这个新国家的存在。
第七章 自由的帝国,贸易的帝国
一种全新的世界主义随之兴起。新教徒和资本主义北欧所形成的新兴帝国,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散布全球。不同的是,他们至少在名义上都是贸易帝国,儘量避免殖民和征服,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以财富而非军事的力量来发展。
第八章 奴隶制度
现代奴隶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与古代及中古时代相当不同。它开始于1444年8月8日的早晨,当时载有235名非洲人的第一批货船从今天的塞内加尔出发,在葡萄牙的拉哥斯港上岸。赞助航海事业的航海家亨利王子,从所有的奴隶中挑选出最好的五分之一,然后骑马离去,“黑金”贸易从此开始。
第九章 终极边疆
太平洋上的岛屿并不单是布乾维尔与康默森所描述的那般俗气逸乐,那里也是提供欧洲商船补给的地方,是前往传说中南方大陆的那条航线上的潜在据点。在西班牙的虎视眈眈之下,英法两国对南方海洋的潜在财富有着不确定但相当明显的计画。
第十章 帝国、种族、国家
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还是继续致力“教化野蛮人”。并藉此使世界各民族
结合为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总有一天,世界上被殖民的民族一定会“开化”。当那一天到来,他们必然要取回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结语
人物表
序言
序
这是一本很简短的书,但主题却很庞大──大到可以直接称呼为世界历史。这是许多民族转变为庞大国家组织,即所谓“帝国”的故事。我们有意定义该词──儘管如此,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定义──非洲、亚洲、美洲、欧洲都一直存在帝国。然而,我主要关注的是今天所说的西方世界的帝国,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崛起一直到苏联的瓦解。我只在与西方帝国故事有关之处,才讨论到中国、毗迦耶那迦罗王朝、伊朗的萨非王朝。这并不是因为我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认为中国人、印度人与伊朗人绝对缺乏创造力、想像力和个体性;一般认为欧洲人因为拥有这三种特性,而能统治世界大部分的领土。这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有自身的历史,有时这些历史是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而这部分需要其他专着来详述。
就像所有试图涵盖许多地域并横跨数段历史的书籍一样,写本书时我必须依赖同事与朋友的帮助,为我提供信息与建议。罗威(Bill Rowe)与罗勒(Matthew Roller)很有耐心地分别回答了我关于中国与罗马世界的问题。我从苏伯拉罕雅(Sanjay Subrahmanyam)与古伦辛斯基(Serge Grunzinski)学到如何以世界性的眼光去思考,还有关于印度、伊朗、拉丁美洲等地的国别史。我尤其要感激我课堂上的学生。我在华盛顿约翰霍普开设“帝国与帝国主义”,那些学生提供我许多信息,质疑我许多模稜两可的主张,这种有着多种语言的国际性课堂中,教会了我很多曾坐立不安的东西。这本书的初稿得到蒙第(Toby Mundy)与摩尔斯(Scott Moyers)的仔细阅读,他们的评论对本书定稿的帮助难以估量。我很感谢他们的耐心与敏锐。我同样感谢威尔森(Rebecca Wilson)与杭特(Alice Hunt)在最后阶段的帮助。
西萨(Giulia Sissa)教导我古希腊文,还有关于人生的一切,我以感激的心将此书献给她。
巴黎 2000年8月
这是一本很简短的书,但主题却很庞大──大到可以直接称呼为世界历史。这是许多民族转变为庞大国家组织,即所谓“帝国”的故事。我们有意定义该词──儘管如此,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定义──非洲、亚洲、美洲、欧洲都一直存在帝国。然而,我主要关注的是今天所说的西方世界的帝国,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崛起一直到苏联的瓦解。我只在与西方帝国故事有关之处,才讨论到中国、毗迦耶那迦罗王朝、伊朗的萨非王朝。这并不是因为我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认为中国人、印度人与伊朗人绝对缺乏创造力、想像力和个体性;一般认为欧洲人因为拥有这三种特性,而能统治世界大部分的领土。这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有自身的历史,有时这些历史是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而这部分需要其他专着来详述。
就像所有试图涵盖许多地域并横跨数段历史的书籍一样,写本书时我必须依赖同事与朋友的帮助,为我提供信息与建议。罗威(Bill Rowe)与罗勒(Matthew Roller)很有耐心地分别回答了我关于中国与罗马世界的问题。我从苏伯拉罕雅(Sanjay Subrahmanyam)与古伦辛斯基(Serge Grunzinski)学到如何以世界性的眼光去思考,还有关于印度、伊朗、拉丁美洲等地的国别史。我尤其要感激我课堂上的学生。我在华盛顿约翰霍普开设“帝国与帝国主义”,那些学生提供我许多信息,质疑我许多模稜两可的主张,这种有着多种语言的国际性课堂中,教会了我很多曾坐立不安的东西。这本书的初稿得到蒙第(Toby Mundy)与摩尔斯(Scott Moyers)的仔细阅读,他们的评论对本书定稿的帮助难以估量。我很感谢他们的耐心与敏锐。我同样感谢威尔森(Rebecca Wilson)与杭特(Alice Hunt)在最后阶段的帮助。
西萨(Giulia Sissa)教导我古希腊文,还有关于人生的一切,我以感激的心将此书献给她。
巴黎 2000年8月
后记
英国人迅速勘察太平洋、在澳洲与纽西兰建立殖民地的举动,在18世纪末扩张了欧洲的影响力,以及欧洲海权在全世界的界线。欧洲人顺利地以他们的方式建立霸权,直到20世纪中期。他们的竞争者只剩下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末的国力虽然明显衰弱,但进入19世纪时仍足以维持独立自主。奥斯曼苏丹试图在所谓的“大博弈”[1]中挑拨离间,阻止欧洲人的入侵,随后摇摇晃晃地撑到19世纪末。到了1900年,古代苏丹的地位已所剩无几;1908年,一群自由派改革者“青年土耳其党人”夺取了这个位置,试图将国家改变为现代的共和国[2]。
虽然中国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庞大贸易伙伴,然而,当马戛尔尼代表东印度公司与乔治三世在1793年造访中国时,它在贪婪的英国人眼中已显得非常脆弱。现今人们大多记得马戛尔尼拒绝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传统的磕头礼仪[3]。不过,马戛尔尼的违抗并不只是个人荣誉的问题。大使在必要时会把个人尊严摆在一旁;马戛尔尼就是一位很好的大使。拒绝在天朝之子面前卑躬屈膝,其实是他传达信念的方式:在他眼中,一个多疑、内向、保守的文明,将无法长期抵挡自由贸易的力量──最后也绝对无法抵挡西方科技的力量。中国很明显是个古老、停滞的社会。德国哲学家赫德说,它像“身处于世界边缘的老旧遗蹟”[4]。要有人推它,它才会往前走。创新、不拘形式、怀抱个人主义的欧洲人,当然就是负责推它的人。
几年之内,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漫无节制地向中国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给“恶魔般的外国人”,最终导致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
英国人扩展了他们在香港的基地,还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他们认为西藏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59年,英国人设立了总税务司,它是一个隶属于中国皇帝的庞大官僚组织,实际上却以英国的商业利益在运作。德国在中国北方建立基地,已经占领印度尼西亚的法国则在中国的南方扩展影响力。
1900年,英、法、俄、意、德、美、日(当时已经占领朝鲜和台湾)共同平定义和团之乱,并掠夺北京。经过一连串的侵略之后,这个从成吉思汗时代就持续存在的帝国,在1911年因一次内部的叛变而崩解,由一群地区性指挥官(称为军阀)夺得了统治权,直到1949年共产党接手为止。
强大的中华帝国灭亡后,整个世界落入了欧洲列强、俄罗斯、美国三方的手中。1800年,这些势力大致占有或控制了地球表面的35%;1878年,扩张到67%;到了1914年,已经超过84%[5]。然而,一如过去所有帝国,这些霸权开始逐渐衰弱。到了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大抵是西方强权为了自利而彼此争战,西班牙的政治人物马达里亚加曾称为“欧洲的两次大型内战”[6]──之后,帝国霸权力量明显地走向终结。
20世纪欧洲的新兴帝国,即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自称的帝国,在短短几年内先盛后衰。另一个帝国是苏联,对西方而言它是曾由沙皇统治的古老帝国的扩大,因支撑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而衰落;对东方而言,它苟延残喘地活着。欧洲的海外帝国在1947年到1960年代末之间全数消失。英国仍然拥有14个殖民地,只不过官方名称是“属地”──英国仍统治北爱尔兰则备受争议。大英国协宛如柏克口中“自由的帝国”的终曲,继续破碎地唱着。法国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依然保有殖民地。西班牙则保住北非海岸的休达和美利拉[7]。但这些大多已是消逝中的记忆了。
欧洲现代帝国的衰落与过去崛起的速度一样迅速,而大部分的衰落原因都极为类似。所有帝国最后都是以默许,而非以武力或威胁以武力来维持统治。过去的确发生过一些卑劣的事件,例如1857年英国对“印度兵变”的镇压行动,但它本质上没有改变英国人与印度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适用于罗马帝国的同样适用于英国、法国、德国,甚至俄国:只要被统治者中有一定数量的人能取得某些统治利益,他们就会想要维持被统治的状态。
此外,19世纪初兴起的这些帝国不同于以前的帝国,它们几乎不会把本国人民输出到殖民地(南非是例外),或者产生很多有能力对抗当地暴动的克里奥尔精英分子。
抵抗任何统治都必须有组织与勇气。但为了抵抗殖民统治,还需要有一种未来会更好的愿景。它需要某种意识形态,能够动员那些準备继续接受现状、认为现状无可避免的人。讽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正是驱动多数现代帝国主义的社会改造过程所产生的,也就是民族主义。在麦考利勋爵所谓的“欧洲制度”中,大部分20世纪被殖民者唯一想要的,是独立的民族国家。
欧洲各帝国让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国阶级的低阶人民。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民族自决”的西方概念。从爱尔兰到爪哇,“民族”一词似乎提供了政治学家安德森所谓的“想像的共同体”,虽然这个共同体没有旧式社会、教区或村庄等的特质,但却让人们期望归属于一个範围更大、可能更有力量的团体[1]。
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共同体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
人们普遍相信,共同体所存在的领土必须与大多数居民的语言、种族等有一致的关係。在极端的例子中,某些说着其他语言或是属于其他种族的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如果他们不肯走,甚至可能会被消灭。“种族净化”绝不是后苏联世界才发明出的产物。当然,民族必须自己统治自己。“只有完全独立的国家才能达成民族自决”的观念出现在1870年代,当时许多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如义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和爱尔兰人,想要从奥匈帝国、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来。在追求民族认同的过程中,这个观念成了一个理想──巴斯克与科西嘉的极端主义者至今仍相当坚持。
相同的理想与期待要在欧洲海外的属地扎根,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当它们真的扎根,却招来毁灭性的后果。从一次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中期,短短期间内,各属地民族所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清除了大量的帝国时代建筑。某些地方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还保有一些尊严时,就承认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离开殖民地,而没有付出太多代价。英国人仓促地从非洲、加勒比海地区离开,留下十分不稳定的岛国经济,只能靠美国的观光客来拯救。葡萄牙的果阿最后在1961年被印度军队占领。香港是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在1997年归还给中国;当时举行了一场仪式,以“吉尔伯特与苏利文”的音乐当背景,象徵这个日不落帝国的谢幕。另一方面,葡萄牙在亚洲的最后一个工厂“澳门”,在两年后的回归几乎没有人注意。
然而,其他地方──比属刚果、阿尔及利亚、塞普勒斯、罗德西亚(1965年被白人移民占领)、安哥拉、莫三比克──脱离宗主国的过程却很残暴,且历经很长的时间。殖民地战争、追求独立的战争、争取恢复民族地位的战争,是20世纪前六七十年持续上演的戏码,它们所树立的敌意可能一直存留到21世纪的前半。
去殖民化的种种过程,留下的不只是痛苦的记忆与永不磨灭的仇恨。
对这些新兴国家而言,它有时也形成看来难以克服的困境。原因在于,“国家”是一个新兴的和全然欧洲式的观念,而且多数殖民地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并不存在。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古代世界。西班牙、不列颠和高卢都是罗马帝国的不同产物;义大利本身也是。现代的东欧与中欧国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保护之下形成的。现在中南美洲各国的边界,即源自当初西班牙总督行政区的分界。现今大多数东欧与中欧各民族的分布状态,正是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或苏联的产物。
欧洲各帝国在亚洲与非洲各地留下更明显的痕迹,对其后续发展也有更深远的影响。在这里,帝国将几乎没有共同点的民族聚集在一起。有时候,他们只是在一群相异或相互敌对的民族的土地四周划上界线;有时候,则採取强迫或自发性的移民活动。这一点在非洲最明显。非洲是一块被欧洲劫掠者及错误的种族观念所共同践踏的土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不同于印度或亚洲大部分地区,甚至也不像古代的墨西哥与秘鲁,它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间接统治的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假设非洲人有所谓的“部落”。但是,因为非洲多数地区的种族非常複杂,部落的规模区分不是太小,就是太大。萨伊的班贾拉族、肯亚的巴鲁伊亚族和吉库尤族、乌干达的巴吉苏族、奈及利亚的优鲁巴族和伊布族,基本上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伊布族就是虚构出来的单一种族的“部落”,它将所有讲任何一种伊布土话的奴隶集结在一起。如此的分类方式确实能使地方官员的任务变得轻鬆。但是,英国、法国、比利时与德国在非洲殖民地加强行政区域的划分,形成了后来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边界,并在长期带来了悲惨的结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从不存在的种族分界与种族冲突,迅速地成为──而且持续是──这块大陆的主要特色。
几乎所有的现代后殖民国家,都是前帝国政府如此创造出来的。在辛巴威,今天的布拉瓦约市的学童,仍然会聚集在马托波斯山丘上的罗德斯坟墓之前;当以前的国家是罗德西亚时,他们也会这样做。他们会这幺做不是因为他们的师长与父母仍眷恋英国的统治,而是因为如果没有罗德斯,他们就没有现在这个国家[9]。试图将现在的辛巴威与穆胡马塔巴帝国产生连结,以作为国家的基础,已经证明了毫无说服力(穆胡马塔巴帝国在16世纪达到高峰,是辛巴威最骄傲的遗产)。辛巴威是由罗德斯创立、由穆加贝总统继承的国家。
无可避免地,殖民地的民族已经发现,反殖民主义与集体认同并非同一件事。让泰米尔人、马来人、中国人、克伦人、锡克人、孟加拉人、尼洛特人、优鲁巴人或阿善提人认同自己不是英国人,要比让他们想像自己是斯里兰卡人、马来西亚人、缅甸人、印度人、苏丹人、奈及利亚人或迦纳人来得容易许多[10]。19世纪初,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努力建立一个现代的秘鲁国家——结合白种的克里奥尔人与印加帝国的人民——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所有说盖丘亚语的印第安人都“受洗”为“秘鲁人”。民族主义者屡次使用这种极端的方法,而且他们都有很好的理由仿效义大利国民教育部长马丁诺在1896年击败阿度亚时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创造了义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义大利人。[11]”
创造义大利人、印度人、赛普勒斯人或是马来人,后来都证明是不可能的任务。一旦帝国体制崩溃,一旦新国家随着国旗、国歌、货币及邮政所形成的集体认同而成立,一旦政治精英出现或是快速地凝聚在一起,一旦这一切都已经成熟,而帝国主义者与大多数殖民者返回原来的“家”──那幺帝国曾经压抑的旧的分界,以及刻意创设的新的分界,便会进一步分裂这些“新兴”国家,产生更小型的国家和种族群体:印度、巴基斯坦、奈及利亚、赛普勒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摆脱英国统治后,都曾经分割和再分割。越南与中非大部分地区在驱逐法国人之后,部分西非地区在脱离葡萄牙之后,也都是如此。新兴国家可以藉由政客卖弄文笔而产生,但新兴民族的出现要花更久的时间。
殖民地不是唯一经历上述过程的地区。以欧洲而言,18世纪末在帝国边缘开始发生的事,以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曾经警告过的另一种方式,于21世纪悄悄回头改变了帝国中心。17世纪的菲力普三世与四世的首相、18世纪的开明君主查理三世、19世纪的自由派人士,还有20世纪野蛮残忍的佛朗哥将军,都曾经试图融合“西班牙”境内的加泰隆尼亚人、巴斯克人、卡斯提尔人、安达鲁西亚人及加利西亚人,不过最后全部失败。“西班牙”由一个君主统治,他以国家之名掌握权力,不过就如他自己所言,短短二十多年内,这个国家已经是欧洲第一个联邦国家。至于英国,在18世纪初合併成联合王国后,虽然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似乎拥有长期的稳定性,它现在也难以阻挡分裂。这种现象被称为“内部的去殖民化”,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停止,也不知道我们最后会选择何种理想的辞彙去称呼一个“民族”。
然而,并非只有克里奥尔人、土着居民及地方分离主义者会在帝国持续分裂的过程中提出要求。由于“西方人”不再坚持自己有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开发中国家的心态也普遍变得暧昧,世界上的土着居民,例如美国、澳洲、纽西兰的土着居民,便开始坚持某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至于由克里奥尔人统治的国家,包括阿根廷(直到30年前还否认有任何被征服的群体)和加拿大,都修正他们的宪法,并重新检视原始的殖民契约。土着居民试图恢复领土与历史认同的权利,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马博案”。1982年,住在托雷斯海峡穆瑞群岛上的马扬部落,派出三位代表马博、帕西与莱斯,向澳洲最高法院抗诉控告昆士兰省,他们宣称:“马扬人是这些岛屿的主人,是唯一能够享受这些土地的人;这些岛屿从来不是‘王室的领土’。”为了陈述他们的观点,他们进一步提出1788年的权利主张是无效的,该主张说澳洲是“无主地”,任何人想要就可以占领。1992年,澳洲最高法院做出支持他们的判决,因此澳洲联邦丧失的不只是对穆瑞群岛的统治权,也意谓着丧失整块大陆的统治权。1993年12月,“土着居民所有权法案”颁布。它虽然没有将整个澳洲交还给土着居民,却提出方法来补救最高法院法官所谓的“令人非常羞耻的国家遗产”,即欧洲殖民者对付土着居民的历史。
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宣洩的经历,被迫认同这些克里奥尔国家从来没有成立统一过。迄今,也只有少数的民族试图从所在的国家中去争取完整的自主权(1999年在加拿大北部建立的因纽特领地,虽然有仪式与宣言,但充其量只是一个自治省而已)。所有的土着居民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个世界的民族。印第安的密克马克族同时是加拿大人,毛利人同时是纽西兰人。他们拥有两种文化,而且常常必须在某个文化的法律下保护另一种文化。他们也不否认文化具有渗透性,需要定期且大幅度的更新,就像土着居民发言人经常更换一样。这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大多数的主张都强调要延续文化的差异。但很少有文化像他们一样多元。土着居民文化安顿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欧洲文化,如今成为各地的次文化。你无法只靠着乡愁来摆脱数百年来的压抑与卑屈。
弔诡的是,土着居民面对的困境竟与一些民族极为相似。这些民族宁愿不在原来的家乡生活,而移往曾占领他们的帝国的首都。从前欧洲的殖民者飞往美洲、非洲和亚洲,而如今愈来愈多亚洲人、非洲人及加勒比海民族飞去欧洲。他们不像过去的孤立移民团体。他们进行的是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可说是正在移动中的民族,而欧洲从罗马帝国后期以来就未曾经历过这样的移民。某些大型小区几乎是以自给自足的状态在成长──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巴黎的巴尔贝斯区,还有几乎到处都有的中国城。这些小区都坚持家乡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和信仰,更不用说服装、语言与食物了。
但即使在这些小型文化圈中,文化也无法长久维持整体性。第一代移民或许会儘可能将自己隔绝于周围更大的世界。但下一代普遍会想要更多的东西。他们仍认同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但或许也更明确地把自己视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因此,在许多传统欧洲帝国的首都内,包括伦敦和里斯本,种族融合与通婚已经存在相当久,且渐渐形成真正的多种族社会。国家边境与中央首都不再像过去差异那幺大;未来,差异甚至可能进一步缩小。
虽然中国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庞大贸易伙伴,然而,当马戛尔尼代表东印度公司与乔治三世在1793年造访中国时,它在贪婪的英国人眼中已显得非常脆弱。现今人们大多记得马戛尔尼拒绝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传统的磕头礼仪[3]。不过,马戛尔尼的违抗并不只是个人荣誉的问题。大使在必要时会把个人尊严摆在一旁;马戛尔尼就是一位很好的大使。拒绝在天朝之子面前卑躬屈膝,其实是他传达信念的方式:在他眼中,一个多疑、内向、保守的文明,将无法长期抵挡自由贸易的力量──最后也绝对无法抵挡西方科技的力量。中国很明显是个古老、停滞的社会。德国哲学家赫德说,它像“身处于世界边缘的老旧遗蹟”[4]。要有人推它,它才会往前走。创新、不拘形式、怀抱个人主义的欧洲人,当然就是负责推它的人。
几年之内,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漫无节制地向中国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给“恶魔般的外国人”,最终导致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
英国人扩展了他们在香港的基地,还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他们认为西藏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59年,英国人设立了总税务司,它是一个隶属于中国皇帝的庞大官僚组织,实际上却以英国的商业利益在运作。德国在中国北方建立基地,已经占领印度尼西亚的法国则在中国的南方扩展影响力。
1900年,英、法、俄、意、德、美、日(当时已经占领朝鲜和台湾)共同平定义和团之乱,并掠夺北京。经过一连串的侵略之后,这个从成吉思汗时代就持续存在的帝国,在1911年因一次内部的叛变而崩解,由一群地区性指挥官(称为军阀)夺得了统治权,直到1949年共产党接手为止。
强大的中华帝国灭亡后,整个世界落入了欧洲列强、俄罗斯、美国三方的手中。1800年,这些势力大致占有或控制了地球表面的35%;1878年,扩张到67%;到了1914年,已经超过84%[5]。然而,一如过去所有帝国,这些霸权开始逐渐衰弱。到了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大抵是西方强权为了自利而彼此争战,西班牙的政治人物马达里亚加曾称为“欧洲的两次大型内战”[6]──之后,帝国霸权力量明显地走向终结。
20世纪欧洲的新兴帝国,即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自称的帝国,在短短几年内先盛后衰。另一个帝国是苏联,对西方而言它是曾由沙皇统治的古老帝国的扩大,因支撑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而衰落;对东方而言,它苟延残喘地活着。欧洲的海外帝国在1947年到1960年代末之间全数消失。英国仍然拥有14个殖民地,只不过官方名称是“属地”──英国仍统治北爱尔兰则备受争议。大英国协宛如柏克口中“自由的帝国”的终曲,继续破碎地唱着。法国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依然保有殖民地。西班牙则保住北非海岸的休达和美利拉[7]。但这些大多已是消逝中的记忆了。
欧洲现代帝国的衰落与过去崛起的速度一样迅速,而大部分的衰落原因都极为类似。所有帝国最后都是以默许,而非以武力或威胁以武力来维持统治。过去的确发生过一些卑劣的事件,例如1857年英国对“印度兵变”的镇压行动,但它本质上没有改变英国人与印度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适用于罗马帝国的同样适用于英国、法国、德国,甚至俄国:只要被统治者中有一定数量的人能取得某些统治利益,他们就会想要维持被统治的状态。
此外,19世纪初兴起的这些帝国不同于以前的帝国,它们几乎不会把本国人民输出到殖民地(南非是例外),或者产生很多有能力对抗当地暴动的克里奥尔精英分子。
抵抗任何统治都必须有组织与勇气。但为了抵抗殖民统治,还需要有一种未来会更好的愿景。它需要某种意识形态,能够动员那些準备继续接受现状、认为现状无可避免的人。讽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正是驱动多数现代帝国主义的社会改造过程所产生的,也就是民族主义。在麦考利勋爵所谓的“欧洲制度”中,大部分20世纪被殖民者唯一想要的,是独立的民族国家。
欧洲各帝国让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国阶级的低阶人民。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民族自决”的西方概念。从爱尔兰到爪哇,“民族”一词似乎提供了政治学家安德森所谓的“想像的共同体”,虽然这个共同体没有旧式社会、教区或村庄等的特质,但却让人们期望归属于一个範围更大、可能更有力量的团体[1]。
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共同体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
人们普遍相信,共同体所存在的领土必须与大多数居民的语言、种族等有一致的关係。在极端的例子中,某些说着其他语言或是属于其他种族的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如果他们不肯走,甚至可能会被消灭。“种族净化”绝不是后苏联世界才发明出的产物。当然,民族必须自己统治自己。“只有完全独立的国家才能达成民族自决”的观念出现在1870年代,当时许多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如义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和爱尔兰人,想要从奥匈帝国、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来。在追求民族认同的过程中,这个观念成了一个理想──巴斯克与科西嘉的极端主义者至今仍相当坚持。
相同的理想与期待要在欧洲海外的属地扎根,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当它们真的扎根,却招来毁灭性的后果。从一次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中期,短短期间内,各属地民族所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清除了大量的帝国时代建筑。某些地方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还保有一些尊严时,就承认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离开殖民地,而没有付出太多代价。英国人仓促地从非洲、加勒比海地区离开,留下十分不稳定的岛国经济,只能靠美国的观光客来拯救。葡萄牙的果阿最后在1961年被印度军队占领。香港是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在1997年归还给中国;当时举行了一场仪式,以“吉尔伯特与苏利文”的音乐当背景,象徵这个日不落帝国的谢幕。另一方面,葡萄牙在亚洲的最后一个工厂“澳门”,在两年后的回归几乎没有人注意。
然而,其他地方──比属刚果、阿尔及利亚、塞普勒斯、罗德西亚(1965年被白人移民占领)、安哥拉、莫三比克──脱离宗主国的过程却很残暴,且历经很长的时间。殖民地战争、追求独立的战争、争取恢复民族地位的战争,是20世纪前六七十年持续上演的戏码,它们所树立的敌意可能一直存留到21世纪的前半。
去殖民化的种种过程,留下的不只是痛苦的记忆与永不磨灭的仇恨。
对这些新兴国家而言,它有时也形成看来难以克服的困境。原因在于,“国家”是一个新兴的和全然欧洲式的观念,而且多数殖民地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并不存在。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古代世界。西班牙、不列颠和高卢都是罗马帝国的不同产物;义大利本身也是。现代的东欧与中欧国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保护之下形成的。现在中南美洲各国的边界,即源自当初西班牙总督行政区的分界。现今大多数东欧与中欧各民族的分布状态,正是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或苏联的产物。
欧洲各帝国在亚洲与非洲各地留下更明显的痕迹,对其后续发展也有更深远的影响。在这里,帝国将几乎没有共同点的民族聚集在一起。有时候,他们只是在一群相异或相互敌对的民族的土地四周划上界线;有时候,则採取强迫或自发性的移民活动。这一点在非洲最明显。非洲是一块被欧洲劫掠者及错误的种族观念所共同践踏的土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不同于印度或亚洲大部分地区,甚至也不像古代的墨西哥与秘鲁,它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间接统治的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假设非洲人有所谓的“部落”。但是,因为非洲多数地区的种族非常複杂,部落的规模区分不是太小,就是太大。萨伊的班贾拉族、肯亚的巴鲁伊亚族和吉库尤族、乌干达的巴吉苏族、奈及利亚的优鲁巴族和伊布族,基本上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伊布族就是虚构出来的单一种族的“部落”,它将所有讲任何一种伊布土话的奴隶集结在一起。如此的分类方式确实能使地方官员的任务变得轻鬆。但是,英国、法国、比利时与德国在非洲殖民地加强行政区域的划分,形成了后来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边界,并在长期带来了悲惨的结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从不存在的种族分界与种族冲突,迅速地成为──而且持续是──这块大陆的主要特色。
几乎所有的现代后殖民国家,都是前帝国政府如此创造出来的。在辛巴威,今天的布拉瓦约市的学童,仍然会聚集在马托波斯山丘上的罗德斯坟墓之前;当以前的国家是罗德西亚时,他们也会这样做。他们会这幺做不是因为他们的师长与父母仍眷恋英国的统治,而是因为如果没有罗德斯,他们就没有现在这个国家[9]。试图将现在的辛巴威与穆胡马塔巴帝国产生连结,以作为国家的基础,已经证明了毫无说服力(穆胡马塔巴帝国在16世纪达到高峰,是辛巴威最骄傲的遗产)。辛巴威是由罗德斯创立、由穆加贝总统继承的国家。
无可避免地,殖民地的民族已经发现,反殖民主义与集体认同并非同一件事。让泰米尔人、马来人、中国人、克伦人、锡克人、孟加拉人、尼洛特人、优鲁巴人或阿善提人认同自己不是英国人,要比让他们想像自己是斯里兰卡人、马来西亚人、缅甸人、印度人、苏丹人、奈及利亚人或迦纳人来得容易许多[10]。19世纪初,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努力建立一个现代的秘鲁国家——结合白种的克里奥尔人与印加帝国的人民——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所有说盖丘亚语的印第安人都“受洗”为“秘鲁人”。民族主义者屡次使用这种极端的方法,而且他们都有很好的理由仿效义大利国民教育部长马丁诺在1896年击败阿度亚时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创造了义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义大利人。[11]”
创造义大利人、印度人、赛普勒斯人或是马来人,后来都证明是不可能的任务。一旦帝国体制崩溃,一旦新国家随着国旗、国歌、货币及邮政所形成的集体认同而成立,一旦政治精英出现或是快速地凝聚在一起,一旦这一切都已经成熟,而帝国主义者与大多数殖民者返回原来的“家”──那幺帝国曾经压抑的旧的分界,以及刻意创设的新的分界,便会进一步分裂这些“新兴”国家,产生更小型的国家和种族群体:印度、巴基斯坦、奈及利亚、赛普勒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摆脱英国统治后,都曾经分割和再分割。越南与中非大部分地区在驱逐法国人之后,部分西非地区在脱离葡萄牙之后,也都是如此。新兴国家可以藉由政客卖弄文笔而产生,但新兴民族的出现要花更久的时间。
殖民地不是唯一经历上述过程的地区。以欧洲而言,18世纪末在帝国边缘开始发生的事,以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曾经警告过的另一种方式,于21世纪悄悄回头改变了帝国中心。17世纪的菲力普三世与四世的首相、18世纪的开明君主查理三世、19世纪的自由派人士,还有20世纪野蛮残忍的佛朗哥将军,都曾经试图融合“西班牙”境内的加泰隆尼亚人、巴斯克人、卡斯提尔人、安达鲁西亚人及加利西亚人,不过最后全部失败。“西班牙”由一个君主统治,他以国家之名掌握权力,不过就如他自己所言,短短二十多年内,这个国家已经是欧洲第一个联邦国家。至于英国,在18世纪初合併成联合王国后,虽然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似乎拥有长期的稳定性,它现在也难以阻挡分裂。这种现象被称为“内部的去殖民化”,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停止,也不知道我们最后会选择何种理想的辞彙去称呼一个“民族”。
然而,并非只有克里奥尔人、土着居民及地方分离主义者会在帝国持续分裂的过程中提出要求。由于“西方人”不再坚持自己有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开发中国家的心态也普遍变得暧昧,世界上的土着居民,例如美国、澳洲、纽西兰的土着居民,便开始坚持某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至于由克里奥尔人统治的国家,包括阿根廷(直到30年前还否认有任何被征服的群体)和加拿大,都修正他们的宪法,并重新检视原始的殖民契约。土着居民试图恢复领土与历史认同的权利,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马博案”。1982年,住在托雷斯海峡穆瑞群岛上的马扬部落,派出三位代表马博、帕西与莱斯,向澳洲最高法院抗诉控告昆士兰省,他们宣称:“马扬人是这些岛屿的主人,是唯一能够享受这些土地的人;这些岛屿从来不是‘王室的领土’。”为了陈述他们的观点,他们进一步提出1788年的权利主张是无效的,该主张说澳洲是“无主地”,任何人想要就可以占领。1992年,澳洲最高法院做出支持他们的判决,因此澳洲联邦丧失的不只是对穆瑞群岛的统治权,也意谓着丧失整块大陆的统治权。1993年12月,“土着居民所有权法案”颁布。它虽然没有将整个澳洲交还给土着居民,却提出方法来补救最高法院法官所谓的“令人非常羞耻的国家遗产”,即欧洲殖民者对付土着居民的历史。
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宣洩的经历,被迫认同这些克里奥尔国家从来没有成立统一过。迄今,也只有少数的民族试图从所在的国家中去争取完整的自主权(1999年在加拿大北部建立的因纽特领地,虽然有仪式与宣言,但充其量只是一个自治省而已)。所有的土着居民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个世界的民族。印第安的密克马克族同时是加拿大人,毛利人同时是纽西兰人。他们拥有两种文化,而且常常必须在某个文化的法律下保护另一种文化。他们也不否认文化具有渗透性,需要定期且大幅度的更新,就像土着居民发言人经常更换一样。这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大多数的主张都强调要延续文化的差异。但很少有文化像他们一样多元。土着居民文化安顿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欧洲文化,如今成为各地的次文化。你无法只靠着乡愁来摆脱数百年来的压抑与卑屈。
弔诡的是,土着居民面对的困境竟与一些民族极为相似。这些民族宁愿不在原来的家乡生活,而移往曾占领他们的帝国的首都。从前欧洲的殖民者飞往美洲、非洲和亚洲,而如今愈来愈多亚洲人、非洲人及加勒比海民族飞去欧洲。他们不像过去的孤立移民团体。他们进行的是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可说是正在移动中的民族,而欧洲从罗马帝国后期以来就未曾经历过这样的移民。某些大型小区几乎是以自给自足的状态在成长──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巴黎的巴尔贝斯区,还有几乎到处都有的中国城。这些小区都坚持家乡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和信仰,更不用说服装、语言与食物了。
但即使在这些小型文化圈中,文化也无法长久维持整体性。第一代移民或许会儘可能将自己隔绝于周围更大的世界。但下一代普遍会想要更多的东西。他们仍认同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但或许也更明确地把自己视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因此,在许多传统欧洲帝国的首都内,包括伦敦和里斯本,种族融合与通婚已经存在相当久,且渐渐形成真正的多种族社会。国家边境与中央首都不再像过去差异那幺大;未来,差异甚至可能进一步缩小。
名人推荐
帕戈登不着痕迹地将历史观察和故事融为一体。
——着名历史学家 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着名历史学家 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