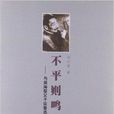
不平则鸣:与周海婴父子谈鲁迅
《不平则鸣:与周海婴父子谈鲁迅》的书稿针对鲁迅研究领域的问题与现象提出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书稿以鲁迅研究领域中流行的“鲁迅精神”的灵魂是“立人”为靶子提出不同意见。作者反驳了“鲁迅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提出在当代社会,“战士的鲁迅”并不过时。
基本介绍
- 书名:不平则鸣:与周海婴父子谈鲁迅
- 出版社:民众出版社
- 页数:300页
- 开本:32
- 品牌:民众出版社
- 作者:冯壮波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501450817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不平则鸣:与周海婴父子谈鲁迅》以鲁迅研究领域中流行的“鲁迅精神”的灵魂是“立人”为靶子提出不同意见。作者冯壮波反驳了“鲁迅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作者简介
冯壮波,1947年生于河北省辛集市(原束鹿县)。1965年1月高中肄业自石家庄市应徵入伍。196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2月由部队转业,1977年12月调入北京市公安局,从事刑事侦察工作,直至退休。曾着有《麒麟皮下的马脚——话说及其他》一书,2009年1月由民众出版社出版。
图书目录
一、周氏父子与“鲁迅精神”
1.从《鲁迅是谁?》说起
2.弘扬“鲁迅精神”不是鲁迅家的私事
3.鲁迅的子孙需要什幺“特殊位置”?
4.周氏父子的“鲁迅精神”
二.毛泽东的“鲁迅精神”
1.鲁迅与毛泽东
2.毛泽东与鲁迅
3.毛泽东的“鲁迅精神”
三.“鲁迅精神”与意识形态
1.“宣传鲁迅精神”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事
2.两种“鲁迅精神”凸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
3.“意识形态化”是什幺化?
4.“立人”没有脱离意识形态
5.“政治意识形态”为什幺“特别重视”鲁迅?
6.鲁迅的孙子没有“意识形态”吗?
四.鲁迅形象与鲁迅精神
1.人的形象与人的心灵
2.教育体制与鲁迅形象
3.鲁迅的两句诗与鲁迅形象
4.“战士形象”与片面性
5.鲁迅的形象该是什幺样?
五.“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什幺 ?
1.和平时期的鲁迅为什幺坐牢?
2.为什幺“还原历史中的鲁迅”?
3.还原哪个阶段的鲁迅?
4.去鲁迅的“革命化”不是“还原历史中的鲁迅”
六.鲁迅精神与“普世价值”
1.价值与普世价值?
2.“普世价值”的属性
3.“普世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4.从金子的“普世价值”说开去
5.是谁创造了“普世价值”
6.“普世价值”如何“普世”
7.什幺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
8.鲁迅的价值与“实用价值”
9.鲁迅是“现代人的价值理念”的代表吗?
10.鲁迅的价值理念不是“普世价值”
11.“普世价值”不钟情于鲁迅
七.关于“捍卫鲁迅”
后记
1.从《鲁迅是谁?》说起
2.弘扬“鲁迅精神”不是鲁迅家的私事
3.鲁迅的子孙需要什幺“特殊位置”?
4.周氏父子的“鲁迅精神”
二.毛泽东的“鲁迅精神”
1.鲁迅与毛泽东
2.毛泽东与鲁迅
3.毛泽东的“鲁迅精神”
三.“鲁迅精神”与意识形态
1.“宣传鲁迅精神”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事
2.两种“鲁迅精神”凸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
3.“意识形态化”是什幺化?
4.“立人”没有脱离意识形态
5.“政治意识形态”为什幺“特别重视”鲁迅?
6.鲁迅的孙子没有“意识形态”吗?
四.鲁迅形象与鲁迅精神
1.人的形象与人的心灵
2.教育体制与鲁迅形象
3.鲁迅的两句诗与鲁迅形象
4.“战士形象”与片面性
5.鲁迅的形象该是什幺样?
五.“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什幺 ?
1.和平时期的鲁迅为什幺坐牢?
2.为什幺“还原历史中的鲁迅”?
3.还原哪个阶段的鲁迅?
4.去鲁迅的“革命化”不是“还原历史中的鲁迅”
六.鲁迅精神与“普世价值”
1.价值与普世价值?
2.“普世价值”的属性
3.“普世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4.从金子的“普世价值”说开去
5.是谁创造了“普世价值”
6.“普世价值”如何“普世”
7.什幺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
8.鲁迅的价值与“实用价值”
9.鲁迅是“现代人的价值理念”的代表吗?
10.鲁迅的价值理念不是“普世价值”
11.“普世价值”不钟情于鲁迅
七.关于“捍卫鲁迅”
后记
后记
2000年,由于身体等原因,我脱离了工作在家闲居。我本以为自己从此跳出了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成了“世外桃源”中人,“阶级斗争”那根弦早就鬆弛了。我本来只食人间烟火,却不想参与世间的是是非非。我倒不是怕惹一身骚,只是因为个人对于这个世界已无所求。我由于无所事事,上网、思考、学习、写作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
2001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我看到一些人的评论文章,想把鲁迅拉下所谓的“神坛”,还原为“人”,其实是意在沖淡、消解乃至批判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把毛泽东与鲁迅对立起来。这让我感到新鲜和不解。可以说,是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
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在2006年作的关于《鲁迅是谁?》的报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政治意识形态”。类似的言论我在“主流”媒体上也看到过。这种文章、书籍已然汗牛充栋,本不值得格外关注。只因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树大招风,才把我这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招了过来。
唐人韩愈云“不平则鸣”,胡适先生很崇尚宋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名句。看了这个报告之后,虽然没有下定“宁鸣而死”的决心,也不相信这点坦白而粗俗的文字能够成为缠绕在自己脖子上的索命绳索,我却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受这种感觉的驱使,我这个老匹夫就上了犟劲,虽不知天有多高,却“欲与天公试比高”,于是开始了本书稿的写作。我拖拖拉拉,直到2010年3月才完成写作。为了寻求法律保护,我随即到北京市着作权局申请作品自愿登记。在当年10月19日,即鲁迅先生忌日那天通过了审查,北京市着作权局颁发了作品登记证。现在本书能够出版,我特别感谢民众出版社及公安部有关部门的领导的理解、鼓励、帮助和支持。
一些人的言论的传播,不能不说是一种宣传,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倾向的“意愿导向”。其影响如何,我不好估计。像老朽这样的人估计不估计也没有多少意义。再说,我也没有估计得恰如其分那样的能力。估计这种事,是很难做到“中庸”的。只要做不到“中庸”,不是被指责为“左”,就是被指责为“右”,说不定会落个破坏“和谐”的罪名。这还真的不好承担。
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不同信仰的人群怎幺可能有统一的价值理念?理念不同,就有矛盾。有矛盾,怎幺可能不发生斗争?这种斗争的发生与发展,不会以谁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斗争,不是共产党或者谁刻意製造出来的,斗争在共产党产生和存在之前就存在着,共产党现在也不是那种斗争的终结者,它能够改变的也只是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它就会伴随着共产党存在一天。有的人可以漠视这种斗争的存在,甚至压制这种斗争的一方,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扑灭这种斗争。在面对斗争的时候,是为了“和谐”而採取“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还是参与其中“作不疲倦的斗争”?我曾经有过犹豫和彷徨。以我的阅历和年纪,虽非“明哲”,何尝不知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是保身之良策?
看到了一些人关于鲁迅的言论,联想到毛泽东关于“读点鲁迅”的讲话,忽然有所感悟。当年,我没有读过马列,识别不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骗子”,不知道什幺是“为了打鬼,藉助钟馗”,这是一个教训。如果不了解鲁迅,也只能任凭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自说自话,愚弄像我这样的平时不怎幺读鲁迅的人。
做人不能不讲良心,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党性。是鲁迅让我看清楚了一些打鲁迅牌的人的真面目,是鲁迅给了我这个神经已经麻木而无所追求的老头子提笔的勇气和力量。
我的文字,不是应景之作,虽然粗糙,却是用心写的,证明我这个普通公民也知“位卑未敢忘忧国”,证明我这个普通党员在自己的普通位置上,也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判断和操守,党性犹存。我能够有今天,完全得益于共产党的培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对于我,这是“立人”之“本”,不敢忘却,也不曾忘却。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坦坦蕩蕩,用不着曲折隐晦、掖着藏着。毕竟,这是一个不同于鲁迅活着的年代。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除了写写这等文字,聊表寸草心以自慰之外,做不了别的。
像这样的作品,或许应该出现在学界。面对“权威”、“名流”、“市场”等,当我写这等文字的时候,思想也在苦苦挣扎,很纠结。某些人能被我“揪住不放”,不是他们没有思想,不是他们没有学问,不是他们的资历不够或阅历不丰富,不是他们没有机会,更不是他们没有写作能力,只因价值理念不同。
对于鲁迅,我没有刻意地、深入地研究,时至今日充其量仍是一知半解。十余年来,努力地想弄清楚“立人”或者说“鲁迅思想”这个问题。这个努力至今还没有完成,还在继续。我其实与周氏父子和某些研究鲁迅的人一样,不过是借“立人”和与鲁迅相关的话题阐发自己的一些与他们不同的想法而已。
“鲁迅思想”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的“批判的武器”。不同的是,我们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不同,批判的对象不同,想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很为“普世价值”论者称道的话: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周氏父子等说话的权利已经得到了“捍卫”。“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的是些什幺人,我不知道。一些人肯定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是不是能够像“捍卫”周氏父子说话的权利那样“捍卫”我说话的权利?这样的问题我或许想都不应该想。期望值越高,失望也就越大,到头来我或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拿那个值得尊敬的洋老头儿的话当“普世价值”。
十余年来,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学习、不断拓展知识领域的过程,是思想不断充实的过程,是认识不断变化和深化的过程。我的生活也因此而多了一点乐趣。学生时代的读书为我的写作打下了一点文化基础,从军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从警培养了我的思维方式,电脑的套用为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自信和执着则源自信仰。没有这种经历和积澱,仅仅凭兴趣,写作是难以进行和继续的。
2012年3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是保证党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思想是导向,是灵魂。”习近平要求“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我的写作是不是在“维护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可以任人评说。由于能力和水平有限,我随时準备修正错误。
冯壮波
2012年3月26日
2001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我看到一些人的评论文章,想把鲁迅拉下所谓的“神坛”,还原为“人”,其实是意在沖淡、消解乃至批判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把毛泽东与鲁迅对立起来。这让我感到新鲜和不解。可以说,是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
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在2006年作的关于《鲁迅是谁?》的报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政治意识形态”。类似的言论我在“主流”媒体上也看到过。这种文章、书籍已然汗牛充栋,本不值得格外关注。只因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树大招风,才把我这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招了过来。
唐人韩愈云“不平则鸣”,胡适先生很崇尚宋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名句。看了这个报告之后,虽然没有下定“宁鸣而死”的决心,也不相信这点坦白而粗俗的文字能够成为缠绕在自己脖子上的索命绳索,我却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受这种感觉的驱使,我这个老匹夫就上了犟劲,虽不知天有多高,却“欲与天公试比高”,于是开始了本书稿的写作。我拖拖拉拉,直到2010年3月才完成写作。为了寻求法律保护,我随即到北京市着作权局申请作品自愿登记。在当年10月19日,即鲁迅先生忌日那天通过了审查,北京市着作权局颁发了作品登记证。现在本书能够出版,我特别感谢民众出版社及公安部有关部门的领导的理解、鼓励、帮助和支持。
一些人的言论的传播,不能不说是一种宣传,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倾向的“意愿导向”。其影响如何,我不好估计。像老朽这样的人估计不估计也没有多少意义。再说,我也没有估计得恰如其分那样的能力。估计这种事,是很难做到“中庸”的。只要做不到“中庸”,不是被指责为“左”,就是被指责为“右”,说不定会落个破坏“和谐”的罪名。这还真的不好承担。
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不同信仰的人群怎幺可能有统一的价值理念?理念不同,就有矛盾。有矛盾,怎幺可能不发生斗争?这种斗争的发生与发展,不会以谁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斗争,不是共产党或者谁刻意製造出来的,斗争在共产党产生和存在之前就存在着,共产党现在也不是那种斗争的终结者,它能够改变的也只是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它就会伴随着共产党存在一天。有的人可以漠视这种斗争的存在,甚至压制这种斗争的一方,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扑灭这种斗争。在面对斗争的时候,是为了“和谐”而採取“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还是参与其中“作不疲倦的斗争”?我曾经有过犹豫和彷徨。以我的阅历和年纪,虽非“明哲”,何尝不知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是保身之良策?
看到了一些人关于鲁迅的言论,联想到毛泽东关于“读点鲁迅”的讲话,忽然有所感悟。当年,我没有读过马列,识别不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骗子”,不知道什幺是“为了打鬼,藉助钟馗”,这是一个教训。如果不了解鲁迅,也只能任凭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自说自话,愚弄像我这样的平时不怎幺读鲁迅的人。
做人不能不讲良心,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党性。是鲁迅让我看清楚了一些打鲁迅牌的人的真面目,是鲁迅给了我这个神经已经麻木而无所追求的老头子提笔的勇气和力量。
我的文字,不是应景之作,虽然粗糙,却是用心写的,证明我这个普通公民也知“位卑未敢忘忧国”,证明我这个普通党员在自己的普通位置上,也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判断和操守,党性犹存。我能够有今天,完全得益于共产党的培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对于我,这是“立人”之“本”,不敢忘却,也不曾忘却。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坦坦蕩蕩,用不着曲折隐晦、掖着藏着。毕竟,这是一个不同于鲁迅活着的年代。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除了写写这等文字,聊表寸草心以自慰之外,做不了别的。
像这样的作品,或许应该出现在学界。面对“权威”、“名流”、“市场”等,当我写这等文字的时候,思想也在苦苦挣扎,很纠结。某些人能被我“揪住不放”,不是他们没有思想,不是他们没有学问,不是他们的资历不够或阅历不丰富,不是他们没有机会,更不是他们没有写作能力,只因价值理念不同。
对于鲁迅,我没有刻意地、深入地研究,时至今日充其量仍是一知半解。十余年来,努力地想弄清楚“立人”或者说“鲁迅思想”这个问题。这个努力至今还没有完成,还在继续。我其实与周氏父子和某些研究鲁迅的人一样,不过是借“立人”和与鲁迅相关的话题阐发自己的一些与他们不同的想法而已。
“鲁迅思想”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的“批判的武器”。不同的是,我们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不同,批判的对象不同,想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很为“普世价值”论者称道的话: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周氏父子等说话的权利已经得到了“捍卫”。“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的是些什幺人,我不知道。一些人肯定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是不是能够像“捍卫”周氏父子说话的权利那样“捍卫”我说话的权利?这样的问题我或许想都不应该想。期望值越高,失望也就越大,到头来我或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拿那个值得尊敬的洋老头儿的话当“普世价值”。
十余年来,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学习、不断拓展知识领域的过程,是思想不断充实的过程,是认识不断变化和深化的过程。我的生活也因此而多了一点乐趣。学生时代的读书为我的写作打下了一点文化基础,从军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从警培养了我的思维方式,电脑的套用为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自信和执着则源自信仰。没有这种经历和积澱,仅仅凭兴趣,写作是难以进行和继续的。
2012年3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是保证党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思想是导向,是灵魂。”习近平要求“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我的写作是不是在“维护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可以任人评说。由于能力和水平有限,我随时準备修正错误。
冯壮波
2012年3月26日
序言
2006年5月22日,《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是谁?》,署名周海婴、周令飞——鲁迅的儿子和孙子。这是一篇报告稿。对于这篇报告,我是在2008年于网上看到的。此后,我又在南方网和2007年5月29日的《广州日报》中看到,《鲁迅是谁?》获得2006年度广东理论文章一等奖。
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我自从看了周氏父子关于鲁迅的言论报导后,心里就没有平静过。原因倒不是因为周氏父子对鲁迅有什幺独特的见地,而是因为他们的言论代表着鲁迅研究中的一种倾向,甚至是主流,而社会媒体、舆论,钟情于这种倾向。
《鲁迅是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种新的“鲁迅精神”。这种新的鲁迅精神,是对毛泽东1937年提出的鲁迅精神的否定或者说“修正”。
《鲁迅是谁?》是周氏父子的宣言书,他们以报告的形式向世人宣称他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一个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的鲁迅。他们在“还原历史中的鲁迅”的名义下,“还原”的是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树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周树人。他们把“立人为本”看成是“鲁迅精神的灵魂”,用那个时期的周树人沖淡和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鲁迅。
大约在2002年,我在浏览网页时无意中看到鲁迅研究界的一些专家已把“鲁迅思想”的“核心”定位在“立人”上。由于以前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了弄清问题,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对“立人”这个问题的思考上。
什幺是鲁迅思想,这涉及鲁迅到底是个什幺样的人及其思想的本质问题,对鲁迅有兴趣的人应该将此问题弄清楚。单就“立人”作出学理解释,尚属“学术自由”,但如果借题发挥、有意歪曲,情况就比较複杂了。
通过读鲁迅的着作,我知道了“立人”出自鲁迅于1907年留日期间写的《文化偏至论》。在我所看过的鲁迅的全部文章中,也只在这一篇中找到了“立人”二字,即“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当鲁迅用“立人”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饱读诗书的他肯定知道“立人”出自儒家经典,知道在儒家思想中“立人”主要指的是“仁与义”。他是把“立人”作为一个“旧瓶子”,装上了他当时从外国“拿来”的“尊个性而张精神”这种“新酒”、“洋酒”。他的“张精神”,张的是“个人主义”精神。关于这一点,是不会产生歧义的。
周氏父子谈“立人”,好像只愿意突出他“尊个性”那一点。或许他们需要的只是那一点,不需要的当然不会加以理会。他们对于青年鲁迅关于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是“借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批判,对于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的批判都视而不见。他们对于鲁迅所“张”的“精神”,是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探究。至于鲁迅提到的“人国”到底是一个什幺国,更是不见点滴阐述。“人国”,其实是青年鲁迅根据“立人”而推理出来的理想国,是在当时根本不存在,在以后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乌托邦”。那样的“人国”早已被鲁迅放弃,但现在却仍然存在于某些人那坚硬的嘴巴上和爱幻想的大脑中。
《鲁迅是谁?》是战书。周氏父子以“鲁迅精神的灵魂”为“立人”,把鲁迅的思想凝固在1907年,否定了鲁迅的思想是变化的、发展的。仅凭这一点就见其陷入了形上学,就否定了鲁迅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飞跃性的变化,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挑战的不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于另外的一些没有发表过关于鲁迅的言论,没有“话语权”而心目中的鲁迅又与他们父子不同的人们,如我辈,那也是一种挑战。
看来,虽然他们认为是“和平时期”了,说“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了,文坛、论坛却不因此而平静,仍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周氏父子认为“再强调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但是,他们,不只是他们,敢于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述,敢于挑战“政治意识形态”,比起当年被一些人指斥不骂军阀的鲁迅,勇气好像多了几分,战斗精神好像强了几分,比鲁迅好像更像个战士。他们父子对于“跟什幺战?为何而战?”还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什幺样的精神在后面支撑着他(们)去战”。“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战士的周氏父子似正逢其时,正一展战士的风采啊!
鲁迅认为:“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周氏父子的报告,及由报告形成的文章,无疑也是宣传。宣传的不仅是自己关于“鲁迅是谁”的认识,不仅是去鲁迅的“革命化”、去鲁迅的“意识形态化”。而是藉助鲁迅宣传自己的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
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在报纸杂誌上,在课堂上,甚至在会议上,抓住毛泽东的“一点东西”批判一通,调侃一番,争相杯葛毛泽东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三日不见,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是不是经过“独立思考”,不好判断。不过,时至今日,倒是的确没有听说谁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有的人却因此受到追捧,成了出人头地的人。这样的现象恐怕还要一直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父子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本来没有什幺稀奇。他们射向毛泽东的虽然是一支响箭,毕竟晚了半拍,虽非强弩之末,但比起当年《鲁迅与我七十年》披露“毛罗对话”时的轰动效应,已不足道。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受到了奖励。
“战斗一定有倾向。”鲁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斗争倾向,该骂的他不会去夸。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同的“战斗”阵营把他看得都很清楚。其实每个人只要去战斗,都是有倾向的,只是诸如“正人君子”、“第三种人”之类,虽然常常挑起事端,挑衅鲁迅,却以为握有“公理”,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倾向性特别是“阶级性”。周氏父子虽然崇尚“普世价值”,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倾向性。至于他们是不是承认自己的倾向具有“阶级性”,看来他们还没有那个勇气。或许不是没有“勇气”的问题,而是他们压根就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具有“阶级性”。《鲁迅是谁?》的批判没有指名道姓,这或许是显示绅士一样的“宽容”和君子的“仁人之心”,绝不是因为“卑怯”。儘管如此,鲁迅作为研究的客体,夹在周氏父子与毛泽东之间,在“鲁迅是谁”、“鲁迅精神的灵魂”等问题上,泾渭分明,战斗倾向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明显,所以连我这样没有读过多少书,平素里忙于琐事,不敢妄谈意识形态的人也看出了他们的不同。在“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了”的今天,周氏父子让人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另类意识形态,不同于鲁迅的战士形象的另类战士形象。
作为一个凡人,我自知做不到揪着自己的头髮离开这多事的地球,远离喧嚣的尘世,到外星球躲清闲。虽然不能像鲁迅那样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却很想淹没在市井之中,像鲁迅那样“管他冬夏与春秋”。闲暇时的读书、上网,不过是为了驱赶孤独和寂寞,等待天堂的召唤。无奈,我六根不净,常常被一些挑战性极强的文章搅得心绪不宁,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几乎把我这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子逼得为鲁迅“发烧”,为鲁迅狂,几近痴迷,拿得起,放不下,不能自拔。凡是关于鲁迅的文字总想多看一眼,对于鲁迅子孙的文章,我自然不能错过,毕竟他们是与鲁迅有着“天然”关係的人。谁知不看那些文章对他们还没有看法,看后却不由得产生一些想法。从《鲁迅是谁?》其文,认识周氏父子其人。
原以为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周氏父子心目中的鲁迅一定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毕竟是与鲁迅有着“天然的最直接而密切的关係”。看后才知道,他们并不是以他们独特的视角讲述一个只有他们才知道的鲁迅,而是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在阐述他们对于“鲁迅精神”这个沉重话题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感到似曾相识,并没有新鲜感。唯一一点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居然也那样评论鲁迅。
2006年3月,我偶然看到了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录《话说周氏兄弟》,他借“立人”批判领导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的“残酷与荒诞”。虽然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不但不曾用“立人”思想批判毛泽东,反而引以为同志。但是,钱理群教授还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教人死”,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没有“人性”,令人匪夷所思。想不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度,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度,在中国文化教育的最高学府,有些人以传播“鲁迅思想”为名义,打着鲁迅的旗号反鲁迅,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篡改鲁迅,其内容之荒谬,逻辑之混乱,态度之张狂,令人读后很受刺激。我曾经疑心自己是不是回到了鲁迅活着的时代。
刺激让我兴奋起来。我来了精神,自不量力地写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话说(话说周氏兄弟)及其他》一书。目的在于“争鸣”。不想,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走“争鸣”之路仍然很艰难,到处是绊脚石。我虽然有“勇气”说自己之想说,一些出版社却没有出版的“勇气”。不知道他们是“怕”什幺,还是在压制不同意见。几经周折,该书才由民众出版社出版。
想不到,周氏父子关于《鲁迅是谁?》的报告,借“普世价值”否定鲁迅精神中对于共产党人最具价值的部分,与《话说周氏兄弟》可谓一唱一和。矛头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毛泽东的“鲁迅精神”。应该说,这是他们在“和平时期”、“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了的今天,从鲁迅的词句中拣出几个来,集合成一种不同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年代提出的“旧”的“鲁迅精神”。在周氏父子看来,毛泽东提出的“鲁迅精神”显然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和“阶级斗争已经淡化”而过时了,因此,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为了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他们才利用与鲁迅拥有的“天然”关係,提出他们“新”的“鲁迅精神”,代替毛泽东的“旧”的“鲁迅精神”。他们这个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给“立人”贴上鲁迅的标籤以张扬个人主义本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奇怪的是有自称共产党人的人,或在体制内,或在体制外,违反宪法、党章中关于国家、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反而振振有词。是他们没有区分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会那幺低估自己的理论水平。如果对于个人主义听而不闻,採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也就罢了,但有的人在为他们助威扬名,有的人分明是在自觉地、有意地替他们做着缴自己“同志”的械的工作。他们的立场如何我无法确定,我也曾怀疑他们就是鲁迅所谓的“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他们究竟是什幺人,一时不好确定。他们想乾什幺,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能够确定的是,我们是不同信仰的人。
面对毛泽东的“鲁迅精神”和周氏父子的“鲁迅精神”,我当然可以保持沉默。沉默与“独立思考”一样,也是个人的一种权利。做一个看客可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会引火烧身。不过,想到鲁迅为了拯救“看客”的灵魂都弃医从文了,我也很想让鲁迅医治和唤醒我那已经麻木和沉睡了的灵魂,于是我放弃了做“看客”的念头,也算是没有枉读鲁迅的书。在不得不作出抉择的时候,我思量再三,决计不改变先前的立场,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从感性到理性,越老越坚,不管他人怎幺看。我相信鲁迅的眼光,站在鲁迅活着的时候所站的那一边。这很可能会让周氏父子不快乐。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为了谁的快乐和不快乐而写作。现在,“普世价值”正在大行其道,此时发发议论,也好看一看坚持“普世价值”的他们如何对待一个“异端”。
在中国,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的指导思想之一,至今仍然写在党章和宪法里。工农大众及知识分子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把他们作为实践者。二者完美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劳苦大众和普通知识分子挺直了腰板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政治基础是“工农联盟”。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个共同的特徵是不承认阶级性,轻视工农大众。把鲁迅,乃至毛泽东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批判为“狭隘的阶级论”,并想以此为自己的思想争取正统地位。只有这样做,他们才可能由一股暗流涌动的社会思潮转化为一种公开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对于鲁迅,毛泽东是评论最多,评价最高,影响最大,宣传最着力的一个人物。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他的评论必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他不仅把鲁迅“革命化”了,而且是把鲁迅“马克思主义化”、“共产主义化”了。这样说其实并不确切,因为鲁迅与共产党走到一起没有受到胁迫。如果他靠近国民党,他的生活可能更自由、更幸福。如果承认这个事实,就应该承认,是鲁迅自己把自己“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共产主义化”的。毛泽东的评价不过是反映了一个事实。那样的鲁迅,是被一些人厌恶的鲁迅。毛泽东思想的敌人和鲁迅的敌人不可能喜欢那样的一个鲁迅。鲁迅活着的时候因此而备受攻击。当鲁迅成为民族的鲁迅之后,在企图毁灭他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一些人则想方设法把鲁迅变成自己的鲁迅,这个鲁迅不同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心目中的鲁迅。当他们那幺做的时候,必然千方百计消除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批判、诋毁毛泽东的鲁迅观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不破不立,不破除毛泽东在研究、评论鲁迅方面形成和确立的权威,怎幺可能产生新的权威?怎幺可能树立起一个“新”的鲁迅形象?一些所谓的“优秀的青年研究者”对于鲁迅的研究和评论,就是在消解和沖淡毛泽东的影响。周氏父子,不过是他们中的两个。与那些人相比,他们只能算是后来人。从《鲁迅是谁?》中,读者唯读出了周氏父子对于毛泽东,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意”,没有读出他们对于鲁迅的新意。
现在,我又看到了与《鲁迅是谁?》类似的文章,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更不是个滋味。周氏父子的报告,没有扭转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却让我在心中产生了“鲁迅怎幺有这等子孙”的想法。我也知道,这是怪不得鲁迅的。是不是要把心中的想法、看法写出来,周氏父子是不是愿意听真话、听实话、听逆耳的话,这都是我曾经有过的犹豫。他们毕竟是我所敬爱的鲁迅的子孙。但是,在不得不进行抉择的时候,鲁迅无疑是我的最爱。鲁迅是鲁迅,鲁迅的子孙是鲁迅的子孙。在《鲁迅是谁?》的问题上,我也只好忽视他们与鲁迅的“天然”关係,把它看成是两个普通的鲁迅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话听说了多年。相信“普世价值”存在的周氏父子恐怕不会承认在学术研究方面谁有什幺特权。好在周氏父子认为“独立思考”是鲁迅的“骨髓”。想到这儿,我的心坚定了许多,也踏实了许多。我的思考起码是“独立”于周氏父子的思考。这大概有点阿Q式的心理。
不得不承认,经过多年的努力,如钱理群教授那样的学者们与周氏父子联手,或着书立说,或作报告、讲演,配合默契,在弘扬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鲁迅精神”,并否定毛泽东的“鲁迅精神”方面卓有成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确立或者正在确立自己的权威。从我的书架上的鲁迅研究着作来判断,他们主导着鲁迅研究的方向。一些青年已经拜倒在了他们的脚下,成为了他们的崇拜者,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做“冬粉”。
既然我把《鲁迅是谁?》看成是战书,我要应战,同样也必须有个战斗的姿态,让自己儘量表现得像个战士,儘量地像“战士的鲁迅”那样去战斗。由于钱理群教授们的存在,“战士的鲁迅”对于我,且不只是我,并没有过时,我以“战士的鲁迅”为榜样。这样的榜样,起码现在还没有谁可以代替。
我虽然在军队当过战士,但是,军营里的战士毕竟不是思想文化界里的战士。周氏父子认为“战士的鲁迅”是“阶级斗争化”的鲁迅,也不愿意承认鲁迅为“战士”,省得让人戴上一顶“阶级斗争化”的帽子。客观而言,有的人,恐怕与周氏父子一样,不喜欢“战士”。“战士”的存在,或许让他们寝食不安,害怕“战士”的学阀、文霸,必欲扼杀“战士”于襁褓之中。
我学无专长,术无专攻,不但没有经过写作的专业训练,更没有参加过思想理论方面的培训。虽然读过高中,那时候并不喜欢文学,虽然没有“怕周树人”的感觉,但的确是“怕文言文”、“怕作文”,而且怕作文在怕文言文之上。高中时候的第一篇作文被判为不及格,至今仍记忆犹新。老师说我的作文就像“挤牙膏”。看来,“怕作文”不只是现在的一些中学生的心态。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进步了,文化生活丰富了,上学花的钱多了,学习的成本高了,据说学校和教学也在不断改革,怎幺现在的中学生居然还与我四十多年前上中学的时候有同样的感觉?唉!他们是怎幺了?还是教育有问题?由于不喜欢写作,参加工作之后,以我当时的“高学历”,虽然有从事文字工作的机会,我却躲躲闪闪,避之犹恐不及。想不到造化弄人,人到老年,为了敬爱的鲁迅,也为了自己,却不得不与文字结缘。对于鲁迅,笔者素无研究。关于鲁迅的文字,不过是触文生情之后的涂鸦之作。在一些学者、教授的眼里可能是语无伦次的“胡说八道”,不值一晒。
关于“鲁迅精神”,我本也没有“独立”的见解,根本就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把陋见写成文字。是周氏父子的《鲁迅是谁?》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促使我把以往的零零碎碎的认识整理出来。写作虽是由《鲁迅是谁?》而引发,要说是专门针对周氏父子也不全对。因为关于“鲁迅精神”的认识早在看到周氏父子的报告之前就有了,周氏父子不是孤立的。他们不过是藉助“鲁迅精神”这个话题表述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我这样浅薄的文化基础和理论修养,用文字表达所思所想,自知力不从心。当过兵的我知道,两军对垒,敌人是不管你装备如何,準备如何的,该进攻时绝不会手软。从钱理群教授及周氏父子那咄咄逗人的字里行间,我闻到了火药味,听到了枪声。不知道为什幺,忽然想到当兵时候的“副统帅”林彪曾经说过一句话:上了战场,枪声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军人讲“枪声就是命令”。面对强势的攻势,我自知人微言轻,我不但没有“普世价值”那样“现代化”的思想武器,也没有“匕首”、“投枪”,只好捡几块砖头、土块,仓促上阵,胡乱扔出去。即使是投不中目标,击不中要害,也不能连比画都不比画一下就逃之天天。我想像个战士一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战斗。战斗已经开始,我并没有胜算。但是,决不会因为自己的没有準备而要求“费厄泼赖”(fair play,指平等、宽容的竞技比赛)应该实行,也不会因为装备的原始而乞求多一点宽容。我知道,强势的他们,斗志正旺,不会罢手。倘使真的乞求,反而自取其辱,给他们平添笑柄。写出这些粗俗的文字,自知没有运用“普世价值”,因此不是拿出来“普世”的。在一个一家之言一统天下的学术“王国”里,显示与他们不一样的存在,只是荒原上的吶喊。除此以外,恐怕也就没有别的意义和价值了。相比之下,文章写得好坏,语句通顺不通顺,表达得準确不準确等“艺术性”、“技术性”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鲁迅说过:“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幺意识。”(《三闲集·(小小十年)小引》)我不是文艺家,与鲁迅本来没有什幺关係。但是读了鲁迅的书,还是想听鲁迅的话。平心而论,我自问还是做到了“直抒己见”,“吐露本心”。这种“己见”与“本心”,仅仅是一己之见,纵然有人讚赏有人讥讽,但那是他们的事。
这年头有人提倡说“真话”,但是,积几十年之经验,我深深地体会到,“真话”并非人人爱听。不管爱听不爱听,不管“普世价值”论者怎幺看,我把想法与看法写出来了,心中还是顿感轻鬆了许多。这大概符合“普世价值”中的“思想自由”。对错是非是自己的事。其中的一些认识,是在周氏父子的激发下形成的,有的则是在看到周氏父子的《鲁迅是谁?》之前就有了。总之,如果没有看到周氏父子关于《鲁迅是谁?》的报告,我是写不出这本书的。
在写《麒麟皮下的马脚》的时候,我看到鲁迅说:“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幺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还说:“做几句不疼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4日》)这次关于“鲁迅精神”的议论,我仍然不想违背鲁迅的教导,也顾不得周氏父子是不是鲁迅的儿子和孙子,说的是轻是重、是深是浅,或许只有他们才体会得出来。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马克思如是说。(《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567页)对于马克思的话有的人可能不认同。但是,不会有谁认为真理害怕争论,害怕批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相信,读者能够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鉴别,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是闲人闲聊,几分调侃,却也有几分认真。满纸荒唐言,近乎痴人说梦。记得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周氏父子或者他们的同道能否给我一个最高的“礼遇”?我不敢期待更多,等待的或许只有俩字儿:挨骂。
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我自从看了周氏父子关于鲁迅的言论报导后,心里就没有平静过。原因倒不是因为周氏父子对鲁迅有什幺独特的见地,而是因为他们的言论代表着鲁迅研究中的一种倾向,甚至是主流,而社会媒体、舆论,钟情于这种倾向。
《鲁迅是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种新的“鲁迅精神”。这种新的鲁迅精神,是对毛泽东1937年提出的鲁迅精神的否定或者说“修正”。
《鲁迅是谁?》是周氏父子的宣言书,他们以报告的形式向世人宣称他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一个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的鲁迅。他们在“还原历史中的鲁迅”的名义下,“还原”的是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树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周树人。他们把“立人为本”看成是“鲁迅精神的灵魂”,用那个时期的周树人沖淡和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鲁迅。
大约在2002年,我在浏览网页时无意中看到鲁迅研究界的一些专家已把“鲁迅思想”的“核心”定位在“立人”上。由于以前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了弄清问题,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对“立人”这个问题的思考上。
什幺是鲁迅思想,这涉及鲁迅到底是个什幺样的人及其思想的本质问题,对鲁迅有兴趣的人应该将此问题弄清楚。单就“立人”作出学理解释,尚属“学术自由”,但如果借题发挥、有意歪曲,情况就比较複杂了。
通过读鲁迅的着作,我知道了“立人”出自鲁迅于1907年留日期间写的《文化偏至论》。在我所看过的鲁迅的全部文章中,也只在这一篇中找到了“立人”二字,即“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当鲁迅用“立人”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饱读诗书的他肯定知道“立人”出自儒家经典,知道在儒家思想中“立人”主要指的是“仁与义”。他是把“立人”作为一个“旧瓶子”,装上了他当时从外国“拿来”的“尊个性而张精神”这种“新酒”、“洋酒”。他的“张精神”,张的是“个人主义”精神。关于这一点,是不会产生歧义的。
周氏父子谈“立人”,好像只愿意突出他“尊个性”那一点。或许他们需要的只是那一点,不需要的当然不会加以理会。他们对于青年鲁迅关于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是“借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批判,对于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的批判都视而不见。他们对于鲁迅所“张”的“精神”,是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探究。至于鲁迅提到的“人国”到底是一个什幺国,更是不见点滴阐述。“人国”,其实是青年鲁迅根据“立人”而推理出来的理想国,是在当时根本不存在,在以后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乌托邦”。那样的“人国”早已被鲁迅放弃,但现在却仍然存在于某些人那坚硬的嘴巴上和爱幻想的大脑中。
《鲁迅是谁?》是战书。周氏父子以“鲁迅精神的灵魂”为“立人”,把鲁迅的思想凝固在1907年,否定了鲁迅的思想是变化的、发展的。仅凭这一点就见其陷入了形上学,就否定了鲁迅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飞跃性的变化,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挑战的不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于另外的一些没有发表过关于鲁迅的言论,没有“话语权”而心目中的鲁迅又与他们父子不同的人们,如我辈,那也是一种挑战。
看来,虽然他们认为是“和平时期”了,说“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了,文坛、论坛却不因此而平静,仍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周氏父子认为“再强调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但是,他们,不只是他们,敢于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述,敢于挑战“政治意识形态”,比起当年被一些人指斥不骂军阀的鲁迅,勇气好像多了几分,战斗精神好像强了几分,比鲁迅好像更像个战士。他们父子对于“跟什幺战?为何而战?”还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什幺样的精神在后面支撑着他(们)去战”。“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战士的周氏父子似正逢其时,正一展战士的风采啊!
鲁迅认为:“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周氏父子的报告,及由报告形成的文章,无疑也是宣传。宣传的不仅是自己关于“鲁迅是谁”的认识,不仅是去鲁迅的“革命化”、去鲁迅的“意识形态化”。而是藉助鲁迅宣传自己的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
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在报纸杂誌上,在课堂上,甚至在会议上,抓住毛泽东的“一点东西”批判一通,调侃一番,争相杯葛毛泽东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三日不见,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是不是经过“独立思考”,不好判断。不过,时至今日,倒是的确没有听说谁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有的人却因此受到追捧,成了出人头地的人。这样的现象恐怕还要一直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父子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本来没有什幺稀奇。他们射向毛泽东的虽然是一支响箭,毕竟晚了半拍,虽非强弩之末,但比起当年《鲁迅与我七十年》披露“毛罗对话”时的轰动效应,已不足道。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受到了奖励。
“战斗一定有倾向。”鲁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斗争倾向,该骂的他不会去夸。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同的“战斗”阵营把他看得都很清楚。其实每个人只要去战斗,都是有倾向的,只是诸如“正人君子”、“第三种人”之类,虽然常常挑起事端,挑衅鲁迅,却以为握有“公理”,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倾向性特别是“阶级性”。周氏父子虽然崇尚“普世价值”,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倾向性。至于他们是不是承认自己的倾向具有“阶级性”,看来他们还没有那个勇气。或许不是没有“勇气”的问题,而是他们压根就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具有“阶级性”。《鲁迅是谁?》的批判没有指名道姓,这或许是显示绅士一样的“宽容”和君子的“仁人之心”,绝不是因为“卑怯”。儘管如此,鲁迅作为研究的客体,夹在周氏父子与毛泽东之间,在“鲁迅是谁”、“鲁迅精神的灵魂”等问题上,泾渭分明,战斗倾向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明显,所以连我这样没有读过多少书,平素里忙于琐事,不敢妄谈意识形态的人也看出了他们的不同。在“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了”的今天,周氏父子让人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另类意识形态,不同于鲁迅的战士形象的另类战士形象。
作为一个凡人,我自知做不到揪着自己的头髮离开这多事的地球,远离喧嚣的尘世,到外星球躲清闲。虽然不能像鲁迅那样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却很想淹没在市井之中,像鲁迅那样“管他冬夏与春秋”。闲暇时的读书、上网,不过是为了驱赶孤独和寂寞,等待天堂的召唤。无奈,我六根不净,常常被一些挑战性极强的文章搅得心绪不宁,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几乎把我这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子逼得为鲁迅“发烧”,为鲁迅狂,几近痴迷,拿得起,放不下,不能自拔。凡是关于鲁迅的文字总想多看一眼,对于鲁迅子孙的文章,我自然不能错过,毕竟他们是与鲁迅有着“天然”关係的人。谁知不看那些文章对他们还没有看法,看后却不由得产生一些想法。从《鲁迅是谁?》其文,认识周氏父子其人。
原以为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周氏父子心目中的鲁迅一定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毕竟是与鲁迅有着“天然的最直接而密切的关係”。看后才知道,他们并不是以他们独特的视角讲述一个只有他们才知道的鲁迅,而是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在阐述他们对于“鲁迅精神”这个沉重话题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感到似曾相识,并没有新鲜感。唯一一点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居然也那样评论鲁迅。
2006年3月,我偶然看到了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录《话说周氏兄弟》,他借“立人”批判领导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的“残酷与荒诞”。虽然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不但不曾用“立人”思想批判毛泽东,反而引以为同志。但是,钱理群教授还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教人死”,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没有“人性”,令人匪夷所思。想不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度,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度,在中国文化教育的最高学府,有些人以传播“鲁迅思想”为名义,打着鲁迅的旗号反鲁迅,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篡改鲁迅,其内容之荒谬,逻辑之混乱,态度之张狂,令人读后很受刺激。我曾经疑心自己是不是回到了鲁迅活着的时代。
刺激让我兴奋起来。我来了精神,自不量力地写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话说(话说周氏兄弟)及其他》一书。目的在于“争鸣”。不想,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走“争鸣”之路仍然很艰难,到处是绊脚石。我虽然有“勇气”说自己之想说,一些出版社却没有出版的“勇气”。不知道他们是“怕”什幺,还是在压制不同意见。几经周折,该书才由民众出版社出版。
想不到,周氏父子关于《鲁迅是谁?》的报告,借“普世价值”否定鲁迅精神中对于共产党人最具价值的部分,与《话说周氏兄弟》可谓一唱一和。矛头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毛泽东的“鲁迅精神”。应该说,这是他们在“和平时期”、“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了的今天,从鲁迅的词句中拣出几个来,集合成一种不同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年代提出的“旧”的“鲁迅精神”。在周氏父子看来,毛泽东提出的“鲁迅精神”显然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和“阶级斗争已经淡化”而过时了,因此,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为了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他们才利用与鲁迅拥有的“天然”关係,提出他们“新”的“鲁迅精神”,代替毛泽东的“旧”的“鲁迅精神”。他们这个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给“立人”贴上鲁迅的标籤以张扬个人主义本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奇怪的是有自称共产党人的人,或在体制内,或在体制外,违反宪法、党章中关于国家、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反而振振有词。是他们没有区分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会那幺低估自己的理论水平。如果对于个人主义听而不闻,採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也就罢了,但有的人在为他们助威扬名,有的人分明是在自觉地、有意地替他们做着缴自己“同志”的械的工作。他们的立场如何我无法确定,我也曾怀疑他们就是鲁迅所谓的“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他们究竟是什幺人,一时不好确定。他们想乾什幺,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能够确定的是,我们是不同信仰的人。
面对毛泽东的“鲁迅精神”和周氏父子的“鲁迅精神”,我当然可以保持沉默。沉默与“独立思考”一样,也是个人的一种权利。做一个看客可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会引火烧身。不过,想到鲁迅为了拯救“看客”的灵魂都弃医从文了,我也很想让鲁迅医治和唤醒我那已经麻木和沉睡了的灵魂,于是我放弃了做“看客”的念头,也算是没有枉读鲁迅的书。在不得不作出抉择的时候,我思量再三,决计不改变先前的立场,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从感性到理性,越老越坚,不管他人怎幺看。我相信鲁迅的眼光,站在鲁迅活着的时候所站的那一边。这很可能会让周氏父子不快乐。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为了谁的快乐和不快乐而写作。现在,“普世价值”正在大行其道,此时发发议论,也好看一看坚持“普世价值”的他们如何对待一个“异端”。
在中国,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的指导思想之一,至今仍然写在党章和宪法里。工农大众及知识分子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把他们作为实践者。二者完美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劳苦大众和普通知识分子挺直了腰板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政治基础是“工农联盟”。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个共同的特徵是不承认阶级性,轻视工农大众。把鲁迅,乃至毛泽东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批判为“狭隘的阶级论”,并想以此为自己的思想争取正统地位。只有这样做,他们才可能由一股暗流涌动的社会思潮转化为一种公开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对于鲁迅,毛泽东是评论最多,评价最高,影响最大,宣传最着力的一个人物。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他的评论必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他不仅把鲁迅“革命化”了,而且是把鲁迅“马克思主义化”、“共产主义化”了。这样说其实并不确切,因为鲁迅与共产党走到一起没有受到胁迫。如果他靠近国民党,他的生活可能更自由、更幸福。如果承认这个事实,就应该承认,是鲁迅自己把自己“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共产主义化”的。毛泽东的评价不过是反映了一个事实。那样的鲁迅,是被一些人厌恶的鲁迅。毛泽东思想的敌人和鲁迅的敌人不可能喜欢那样的一个鲁迅。鲁迅活着的时候因此而备受攻击。当鲁迅成为民族的鲁迅之后,在企图毁灭他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一些人则想方设法把鲁迅变成自己的鲁迅,这个鲁迅不同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心目中的鲁迅。当他们那幺做的时候,必然千方百计消除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批判、诋毁毛泽东的鲁迅观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不破不立,不破除毛泽东在研究、评论鲁迅方面形成和确立的权威,怎幺可能产生新的权威?怎幺可能树立起一个“新”的鲁迅形象?一些所谓的“优秀的青年研究者”对于鲁迅的研究和评论,就是在消解和沖淡毛泽东的影响。周氏父子,不过是他们中的两个。与那些人相比,他们只能算是后来人。从《鲁迅是谁?》中,读者唯读出了周氏父子对于毛泽东,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意”,没有读出他们对于鲁迅的新意。
现在,我又看到了与《鲁迅是谁?》类似的文章,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更不是个滋味。周氏父子的报告,没有扭转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却让我在心中产生了“鲁迅怎幺有这等子孙”的想法。我也知道,这是怪不得鲁迅的。是不是要把心中的想法、看法写出来,周氏父子是不是愿意听真话、听实话、听逆耳的话,这都是我曾经有过的犹豫。他们毕竟是我所敬爱的鲁迅的子孙。但是,在不得不进行抉择的时候,鲁迅无疑是我的最爱。鲁迅是鲁迅,鲁迅的子孙是鲁迅的子孙。在《鲁迅是谁?》的问题上,我也只好忽视他们与鲁迅的“天然”关係,把它看成是两个普通的鲁迅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话听说了多年。相信“普世价值”存在的周氏父子恐怕不会承认在学术研究方面谁有什幺特权。好在周氏父子认为“独立思考”是鲁迅的“骨髓”。想到这儿,我的心坚定了许多,也踏实了许多。我的思考起码是“独立”于周氏父子的思考。这大概有点阿Q式的心理。
不得不承认,经过多年的努力,如钱理群教授那样的学者们与周氏父子联手,或着书立说,或作报告、讲演,配合默契,在弘扬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鲁迅精神”,并否定毛泽东的“鲁迅精神”方面卓有成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确立或者正在确立自己的权威。从我的书架上的鲁迅研究着作来判断,他们主导着鲁迅研究的方向。一些青年已经拜倒在了他们的脚下,成为了他们的崇拜者,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做“冬粉”。
既然我把《鲁迅是谁?》看成是战书,我要应战,同样也必须有个战斗的姿态,让自己儘量表现得像个战士,儘量地像“战士的鲁迅”那样去战斗。由于钱理群教授们的存在,“战士的鲁迅”对于我,且不只是我,并没有过时,我以“战士的鲁迅”为榜样。这样的榜样,起码现在还没有谁可以代替。
我虽然在军队当过战士,但是,军营里的战士毕竟不是思想文化界里的战士。周氏父子认为“战士的鲁迅”是“阶级斗争化”的鲁迅,也不愿意承认鲁迅为“战士”,省得让人戴上一顶“阶级斗争化”的帽子。客观而言,有的人,恐怕与周氏父子一样,不喜欢“战士”。“战士”的存在,或许让他们寝食不安,害怕“战士”的学阀、文霸,必欲扼杀“战士”于襁褓之中。
我学无专长,术无专攻,不但没有经过写作的专业训练,更没有参加过思想理论方面的培训。虽然读过高中,那时候并不喜欢文学,虽然没有“怕周树人”的感觉,但的确是“怕文言文”、“怕作文”,而且怕作文在怕文言文之上。高中时候的第一篇作文被判为不及格,至今仍记忆犹新。老师说我的作文就像“挤牙膏”。看来,“怕作文”不只是现在的一些中学生的心态。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进步了,文化生活丰富了,上学花的钱多了,学习的成本高了,据说学校和教学也在不断改革,怎幺现在的中学生居然还与我四十多年前上中学的时候有同样的感觉?唉!他们是怎幺了?还是教育有问题?由于不喜欢写作,参加工作之后,以我当时的“高学历”,虽然有从事文字工作的机会,我却躲躲闪闪,避之犹恐不及。想不到造化弄人,人到老年,为了敬爱的鲁迅,也为了自己,却不得不与文字结缘。对于鲁迅,笔者素无研究。关于鲁迅的文字,不过是触文生情之后的涂鸦之作。在一些学者、教授的眼里可能是语无伦次的“胡说八道”,不值一晒。
关于“鲁迅精神”,我本也没有“独立”的见解,根本就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把陋见写成文字。是周氏父子的《鲁迅是谁?》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促使我把以往的零零碎碎的认识整理出来。写作虽是由《鲁迅是谁?》而引发,要说是专门针对周氏父子也不全对。因为关于“鲁迅精神”的认识早在看到周氏父子的报告之前就有了,周氏父子不是孤立的。他们不过是藉助“鲁迅精神”这个话题表述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我这样浅薄的文化基础和理论修养,用文字表达所思所想,自知力不从心。当过兵的我知道,两军对垒,敌人是不管你装备如何,準备如何的,该进攻时绝不会手软。从钱理群教授及周氏父子那咄咄逗人的字里行间,我闻到了火药味,听到了枪声。不知道为什幺,忽然想到当兵时候的“副统帅”林彪曾经说过一句话:上了战场,枪声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军人讲“枪声就是命令”。面对强势的攻势,我自知人微言轻,我不但没有“普世价值”那样“现代化”的思想武器,也没有“匕首”、“投枪”,只好捡几块砖头、土块,仓促上阵,胡乱扔出去。即使是投不中目标,击不中要害,也不能连比画都不比画一下就逃之天天。我想像个战士一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战斗。战斗已经开始,我并没有胜算。但是,决不会因为自己的没有準备而要求“费厄泼赖”(fair play,指平等、宽容的竞技比赛)应该实行,也不会因为装备的原始而乞求多一点宽容。我知道,强势的他们,斗志正旺,不会罢手。倘使真的乞求,反而自取其辱,给他们平添笑柄。写出这些粗俗的文字,自知没有运用“普世价值”,因此不是拿出来“普世”的。在一个一家之言一统天下的学术“王国”里,显示与他们不一样的存在,只是荒原上的吶喊。除此以外,恐怕也就没有别的意义和价值了。相比之下,文章写得好坏,语句通顺不通顺,表达得準确不準确等“艺术性”、“技术性”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鲁迅说过:“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幺意识。”(《三闲集·(小小十年)小引》)我不是文艺家,与鲁迅本来没有什幺关係。但是读了鲁迅的书,还是想听鲁迅的话。平心而论,我自问还是做到了“直抒己见”,“吐露本心”。这种“己见”与“本心”,仅仅是一己之见,纵然有人讚赏有人讥讽,但那是他们的事。
这年头有人提倡说“真话”,但是,积几十年之经验,我深深地体会到,“真话”并非人人爱听。不管爱听不爱听,不管“普世价值”论者怎幺看,我把想法与看法写出来了,心中还是顿感轻鬆了许多。这大概符合“普世价值”中的“思想自由”。对错是非是自己的事。其中的一些认识,是在周氏父子的激发下形成的,有的则是在看到周氏父子的《鲁迅是谁?》之前就有了。总之,如果没有看到周氏父子关于《鲁迅是谁?》的报告,我是写不出这本书的。
在写《麒麟皮下的马脚》的时候,我看到鲁迅说:“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幺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还说:“做几句不疼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4日》)这次关于“鲁迅精神”的议论,我仍然不想违背鲁迅的教导,也顾不得周氏父子是不是鲁迅的儿子和孙子,说的是轻是重、是深是浅,或许只有他们才体会得出来。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马克思如是说。(《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567页)对于马克思的话有的人可能不认同。但是,不会有谁认为真理害怕争论,害怕批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相信,读者能够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鉴别,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是闲人闲聊,几分调侃,却也有几分认真。满纸荒唐言,近乎痴人说梦。记得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周氏父子或者他们的同道能否给我一个最高的“礼遇”?我不敢期待更多,等待的或许只有俩字儿:挨骂。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