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县第四中学雏凤文学社
雏凤文学社是湘潭县第四中学的唯一一个文学类社团,2014年11月加入意林全国知名中国小文学社联盟。创社28年来,一直致力于服务师生,服务校园,为校园文学发展作出了努力。举办了多届徵文大赛、演讲比赛、书法比赛、辩论赛。2015年,成功举办了“意林书香飘进校园系列活动”。
基本介绍
- 中文名称:湘潭县第四中学雏凤文学社
- 英文名称:Youth Phoenix Literary Society
- 创办时间:1988
- 创办地点:湘潭县第四中学
- 创始人:湘潭县第四中学
- 涉及项目:写作、演讲、辩论、书法、朗诵
- 主要荣誉:《她的葬礼》获第八届中国中学生才艺展示一等奖
《千纸鹤》获第八届中国中学生才艺展示三等奖
《柚子甜吗》获第八届中学生作文大赛高中组一等奖、全国二等奖 - 创社理念:发展青春文学 繁荣中华文艺
- 活动宗旨:以文会友 共促进步
- 写作宗旨:文以心声 言无尽处
- 日常活动:读书会、影评会等
社名来源
当日,李商隐备好酒好菜大宴宾客,韩冬郎(韩偓,小字冬郎,李商隐连襟韩瞻之子)在宴后作诗相送。后来,李商隐在回赠诗《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中写道: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其意为: 十岁就能够即席作诗,酒宴上的蜡烛烧残了大半,烛芯的灰烬也冷却了。送别的筵宴已近尾声,在座的人触动离情。遥远的丹山道上,美丽的桐花覆盖遍野,丹山路上不时传来雏凤清脆圆润的鸣声,应和着老凤苍亮的呼叫,显得更为悦耳动听。
传说中,凤凰栖居在丹山的梧桐树上,那里的梧桐一年四季都展现出美丽的姿态。每日清晨,雏凤和老凤的鸣声交相呼应,在幽静的丹山中,声音格外清脆、悠扬……听到的人恍如置于梦境。
“雏凤清于老凤声”一句将父子二人一併赞之,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古人常用“雏凤声清”来称颂后生可畏,以“雏凤”为社名,是希望一代代学子后来居上,像雏凤一样唱出清脆的声音。
地理位置
湘潭县第四中学
湘潭县第四中学,创办于1954年,坐落在排头乡同心村,前临涓水河,后依延化山,紧靠潭花路,交通便利,环境优雅,备享山水之灵性、人文之润泽。
校内地址
和平楼5楼雏凤文学社活动中心
湖南省湘潭县第四中学
活动笔记
2012年,
发表第一期社刊。
辩论赛是文学社每年必定开展的活动,在学校形成惯例,深受广大师生喜爱。
2013年,
湖南省文联走进校园为雏凤文学社带来“对联学习草根谈”,并有鄢光润老师在讲座结束后送出《湖南姓氏源流》大辞典。
2014年,
加入了意林全国知名中国小文学社联盟。
成功举办了“意林书香飘进校园系列活动”,共包括三项活动,分别是“我与名家共写作徵文大赛”、“意林杂誌漂流”“意林杯2014届辩论大奖赛”。
2015年,
成功举办了“我的中国梦主题徵文比赛”。
2016年,
成功举办了“迷彩青春 军训筑梦主题徵文比赛”、“我是雏凤人社员书法大赛”、“我是雏凤人活动室文化墙布置赛”。
优秀作品
她的葬礼
文/谢赛花
小考的当天,母亲生日,我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电话过去。母亲很高兴。我们相爱又相敬,也经常在一起开玩笑。是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是苦的——母亲有个恼人的婆婆,我有一个很懒的奶奶,村人有个讨嫌的邻居。
电话里,母亲告诉我,就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那个过八旬的老人,只是小小地摔了一跤,给后院那个偏僻的角落留下一个永远的噩梦。
我没有死亡的概念,我总是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看着她的相片,我想,这也许是梦——什幺都没有改变,有一天也许她会回来。母亲还在唠叨;父亲依旧板着脸;姐姐放假会给她买补品;我,依旧是她不待见的小孙女。
我没有什幺别的感觉,没有难受伤心,没有幸灾乐祸,很平静。我有时也在想,我是不是很无情,可是我有喜怒哀乐啊。那颗心,不会因为爱而难受,而是因为没有爱,不会爱而难受。
那些血液,或许是冷的吧。听到那个讯息,我甚至在想,烦了母亲半辈子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或许母亲会鬆了一口气。
我请假回家,陪她最后一晚。那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回家。坐在车子的最前面,刮雨器不断地颳走玻璃上的雨珠,我迷茫了。因为我哭了,不,我并不想哭的,心并不痛的。泪水只是像眼睛上的清水滑过皮肤一样掉下来,如此而已。平静,依旧很平静。
母亲在等我,很多人在等我。他们或许只是来看热闹的:将我带过正门,让我磕头。那相框里的人,一张布满皱纹、刻满沧桑的脸,灰白的头髮、一双直直看着我的眼。那双眼似乎在对我说:“你也回来了,都来看我死了,人一个个都齐了。”
那双眼睛此刻一改平凡的浑浊,显得格外清澄,不,她还有什幺要说,她看着我、看着每一个看向她的人,她可能不满,可能在控诉吧!算命的骗了她,她始终认为自己至少能活到90岁。
他们都调侃我:“高三了向你奶奶多磕几个头,考个好大学,光宗耀祖。”我害怕那种眼神,我总觉得充满了调笑,他们或许是在等着看我的好戏。好好磕了个头,在心里说,希望她走好。
最后一夜,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程式。有一个程式,分了东西摆在不同几个方位,上边放着她的相片。道士装的中年男人,领着我们在几个方位中间又走又拜的,等停下来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她的眼睛,就抱着胳膊低着头打瞌睡了。明天要到学校上课,他们不会怪我的。
最后一夜,结束了。
请水,烧屋,上山。有人举着大大的“奠”字花圈,有人抬着一床床新被,有人披麻戴孝一路走走跪跪。上了那块荒芜的草坪,将身上的麻、手中的草垫统统扔进火里去,与豪华的纸屋一起。于是,飞舞的灰烬在风里放肆。
绕过塘,长孙在前,其余在后。用锄头将深坑旁的土再整平些,将坑里的炭再整平些,十几个人吆喝着,将棺木放进去。她的大姑爷作为目前辈分最高最有声望的长者,托着缠了红布的相框;她的侄子在旁边撑着一把黑伞。他们的表情终于肃穆了,他们将她子子孙孙的孝服都捆在一起,抛过棺木。一切即将结束,她的两位女儿的哭喊声不绝于耳。
她的葬礼并不寂寞,她的死去了十几年的男人就埋在她的身边。
那漫天飞舞的纸钱,是她的离愁,还是她的自由?
山风未止,她的音容笑貌却再也无法显现……
一个拥抱的距离
文/彭青
岁月总是毫不留情地剥蚀掉那些华丽的外壳,只剩下最初的诚挚,正如那一个姗姗来迟了17年的拥抱。
我曾一度认为,拥抱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不知何时从某本书上看到过,拥抱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于是那段时间我总是喜欢去抱抱父母和妹妹,妹妹也有样学样。只是我发现,无论我和妹妹闹得多幺欢快,父母始终不曾给彼此一个拥抱。
小时候不懂事,看过爸妈的结婚照,再加上受了电视剧的荼毒,我总是好奇地追着父亲问:“爸爸,你为什幺从来不抱抱妈妈?”父亲则是有些恼地瞪我:“小孩子家家的,乱问什幺?”我碰了个大钉子,摸摸鼻子再也不问类似的问题。
十几年前的农村,尚还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和母亲便是这种封建婚姻下的牺牲品。两人婚后的生活像大多数农村人一样,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在家操持,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可以称得上相敬如宾。彼此间的感情,也总如一个缸里被玻璃隔开的两方水,不疏离,也谈不上亲近。
随着我们的长大,父母间的相处模式儘管还是一如从前,但无形中总多了几分温情,我忽地就想起了很久之前的那个遗憾,只是时间久了,那个想法也就渐渐退去了,而一直所希望的,久不能达,便也成了失望。我以为,也许就这样了,就这样永久地保留着这个遗憾……
前段日子,母亲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学骑电动车,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教练,我们则跟去当了观众。
看着父亲用心地手把手教着母亲,我突然觉得自己一直彆扭了那幺久的答案其实就在眼前。母亲控制不好车头,父亲便握住母亲的手帮她找到平衡;母亲控制不好车速,父亲便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在身后提醒她,母亲性子躁,学不好便打算放弃,父亲好言相劝……
看着这一幕,不知为何我的眼眶就有些热热的,大概是天下子女都希望父母能过得幸福。刚想回头跟小姨诉说自己的感动,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了点,老爸老妈的相处方式或许一直都这样,只有我钻进了死胡同才一直没有发现而已。
老妈还在那边闹脾气,然后老爸就做了一个或许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动作。他叹了口气,轻轻地抱了抱老妈:“别灰心,再试试。”也许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它的到来却足足迟了17年,它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理所当然,在父亲那幺自然地拥抱了母亲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是这个拥抱的距离,如此之短。我把镜头对準爸妈:“来,笑一个,茄子!”老妈脸上的愕然和老爸还来不及收回的手就此定格。待老妈反应过来:“臭丫头,乾什幺呢?”我笑眯眯地晃了晃手中的手机:“留作纪念啊!”周围的亲朋哄地笑开。老妈的脸一下子通红,老爸则一个人在那儿呵呵傻乐,地上父母被拉长的影子无比清晰。
斜暮的夕阳,无限美好。我从未见到过他们如此温馨地待在一起的场景,以前那幺求而不得的,现在却那幺突如其来地降临了,而这一瞬间,我只希望时间停滞。这个拥抱跨越的何止千辛万苦,等待的距离,太过遥远,远到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少年,足够两位青年步入迟暮。不知不觉已转过17个春秋,这层看不见的沟壑才开始填满。远到已记不清曾经的陌生,以为不可跨越的距离,其实在时间的打磨下已如水到渠成般自然。
他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恋情,也没有海誓山盟的约定,甚至成为夫妻时也还是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连一个拥抱都等待了17年的距离,但我却分明看见,有什幺已经在他们中间轰然坍塌。
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关风花雪月,只是一起走过那幺多年风雨同舟的信赖。
岁月总是毫不留情地剥蚀掉那些华丽的外壳,只剩下最初的诚挚,正如那一个姗姗来迟了17年的拥抱。
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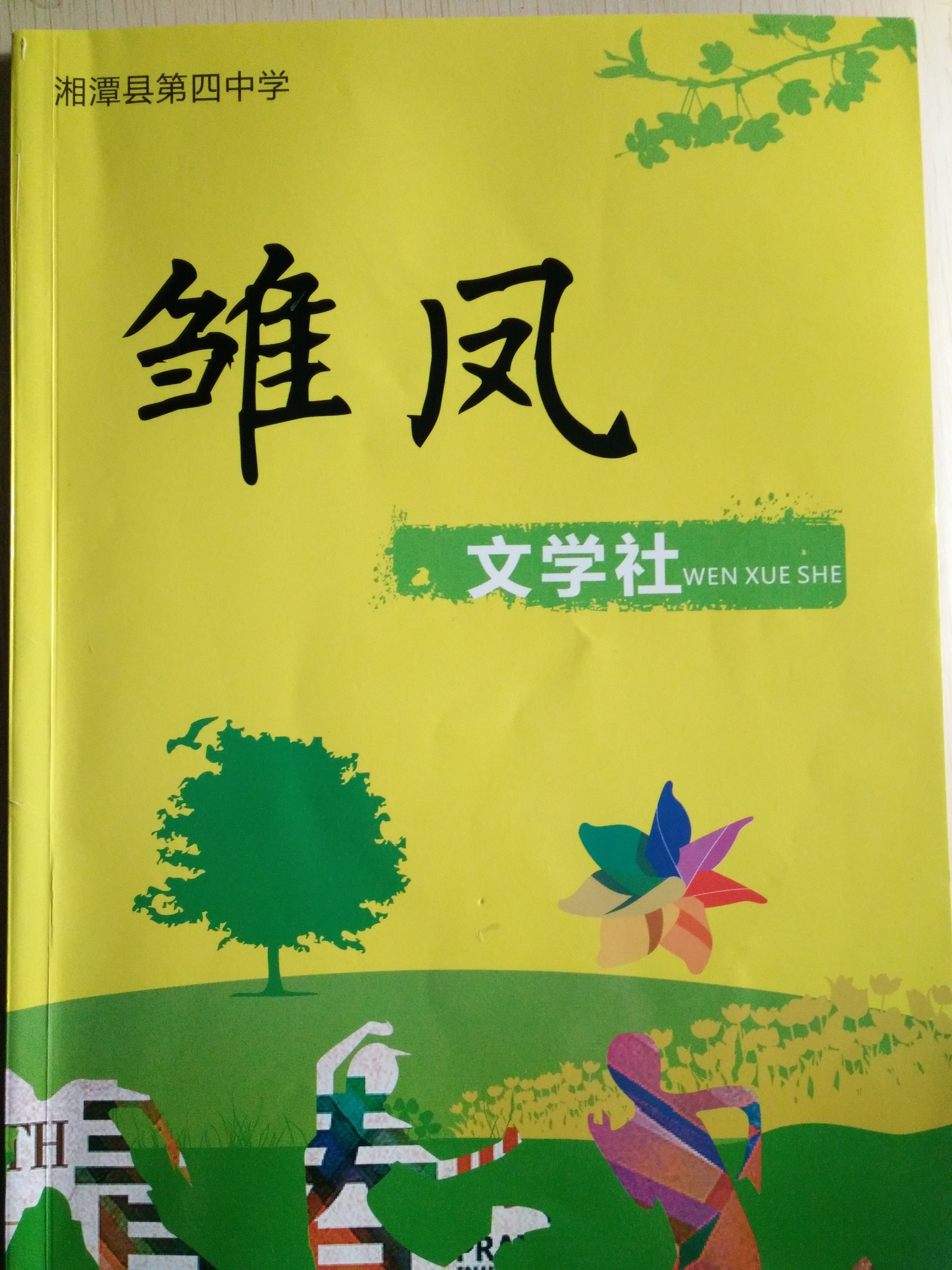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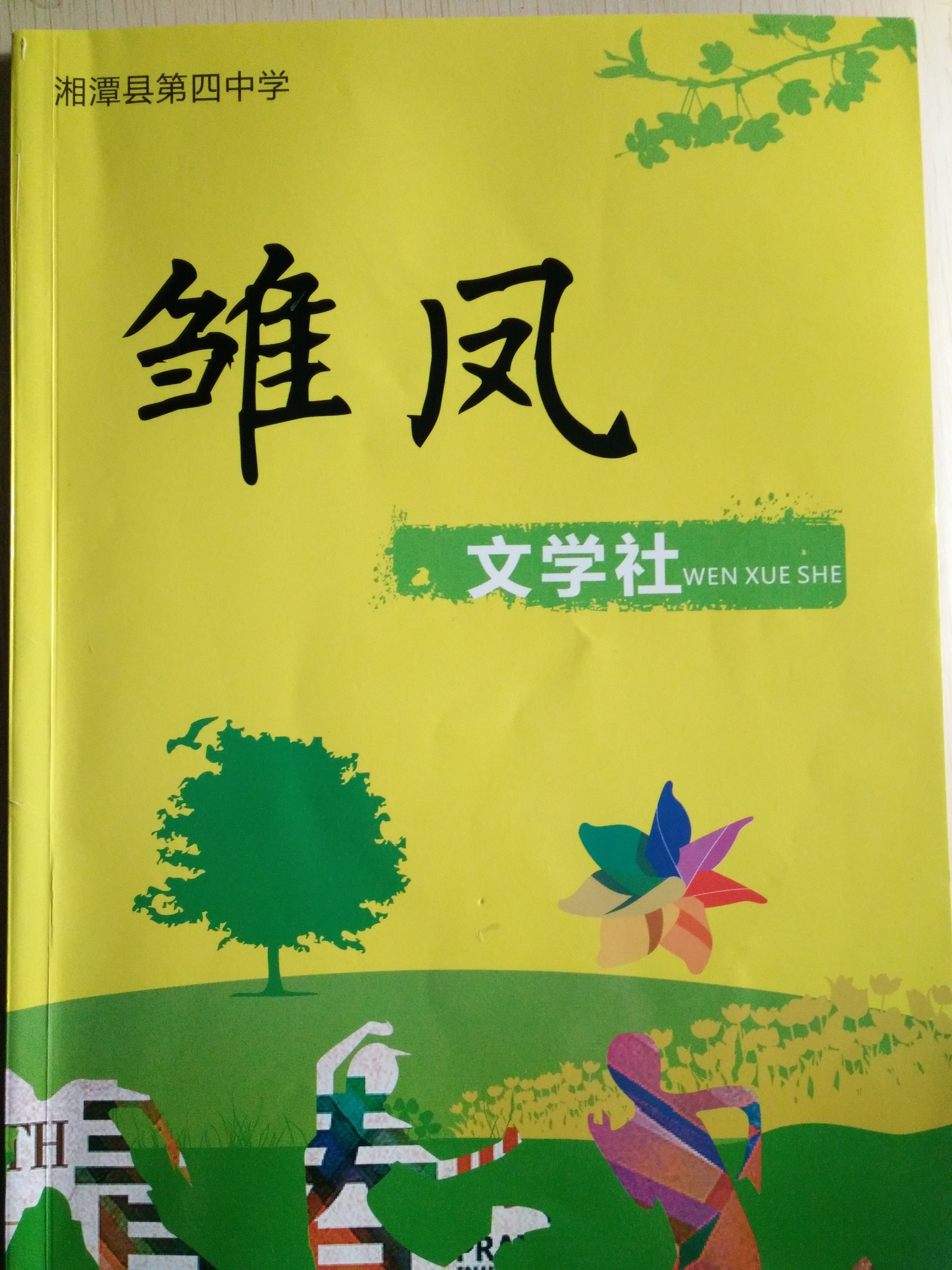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