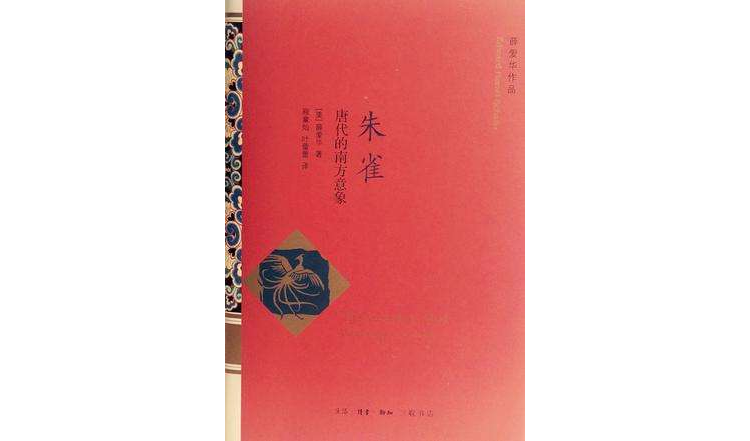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众所周知、在很久以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乾燥炎热的土地上可能存在过繁盛的文明,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博物馆标本。但我们这些温带地区的人却不大会认为潮湿的热带地区有助于人类才能的最佳发挥。这种偏见现今正在被人摒弃。事实上热带雨林和季风海岸、除了滋生衰弱、懒惰、淫蕩和智力迟钝之外,也孕育了众多美好的事物。的确,一千年以前,有许多个伟大文明的中心、都位于亚洲和美洲的热带地区。
基本介绍
- 中文名: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 作者:薛爱华
- 出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 时间:一千年以前
关于作者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以往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係,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绪论
我们钦佩玛雅人、爪哇人、高棉人、僧伽罗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他们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好几个世纪,虽然身处潮湿的森林,却早已繁荣昌盛。当然,那些居住在多雨城市中的深色人种,并不是中世纪精神与物质能量的唯一重大源泉,撇开欧洲不谈,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就以乾旱地带为主,包括波斯、阿拉伯、叙利亚、非洲以及西班牙等地。最后,还有中国,其地理环境属于混合型,从长满山毛榉和云杉的森林,到风沙漫天的沙漠和遍地青草的草原,从温带和亚热带的湖泊区域,再远到鬆散羁縻的边疆垦殖地,那里正是热带区域的起点。最后这片区域正是本书的主题,我尤其要考察其对于中古中国人的知识构成有何贡献,同时考察其对于中国人的感觉、情感以及想像力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考察中国精神这个大熔炉如何改变了这一片土地。
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我经常提到,唐帝国最南端区域的物产,无论是有机物,还是结晶体,在中国人眼中都带有“半异域色彩”。也就是说,这些物产并不像日本、爪哇以及酒矩咤国(梵文对音,意为郁金香)的动植物那样奇异可怕。现在我打算密切关注这一看似矛盾的区域,中国人很久以前就声称这片土地属于他们,但在唐代这个地方对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奇异的。因此,本书是关于中古中国的热带地区,它以朱雀为其象徵,至于朱雀是什幺最终也还是个谜,这个区域同样可以用那个迷人的“越女”形象来作代表,这点会渐渐地显得越发清晰。
无可否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研究呈现的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过去,也就是说,这个过去之特殊化与具体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所特有的。或许所有对过去的再创造都是这种类型的,而我要说的是,在本书中我的目的不是让过去“概念化”(用近来很受追捧的这个抽象词语),而是以一种生动活泼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过去,而且不必牺牲其精确性。这意味着要尝试将唐代人的中世纪世界,既看作是一个实有的境界,又看作是一种想像的诠释。什幺是“真实的”历史,也许言人人殊,我希望我讲述的史事,是诸种可能真实的历史中的一种,我的目的主要在于“实在的”历史。(真实的[true],指与事实相符,与假对应;实在的[real],指客观存在的,与无相对应。)简言之,如果这只“朱雀”最终并非博物馆抽屉里一只剥製好的标本,而是一次可信的复活,儘管它已距今一千年,却还带有某种勃勃生气,那幺,我会真诚地欣幸不已。
我力图一概使用唐代人的史料,以避免因时代倒错而造成对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徵概括显得可笑,只有在注释与阐释时有所例外。由于某一习俗或传说在宋代已存在,进而推测其在唐代即已存在,这样做太过简单。比如,由于马援在十一世纪已成为南方伏波之神,就进而推断他在八世纪即已如此。由于民间传说中有如是之证据,就推测后来对其他信仰、习俗以及制度的记述亦同样如此。我儘可能避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引入某些态度、倾向及选择,它们对宋代人来说很是顺理成章,但对于唐人而言却格格不入,这样的做法十分危险。然而,我偶尔也会参考宋代(甚至元代)的史料,尤其是当它们能够清楚地表明某些先前的习俗或文献当时依然存在的时候。我希望,我这幺做的时候已经足够小心谨慎。
书摘:朱雀
中古时期以朱雀为象徵的国土的历史,已如上述,作为一种动物,也作为一种象徵,朱雀本身同样值得评说。
朱雀是来自远古的意象,唐朝人用它命名神圣的长安城门。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它的出现都是一种上天赐福的吉兆。在中国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有关朱雀、赤燕、赤乌等神鸟的严肃记载。通常,这些徵兆的出现,都伴随着官方对其祥瑞的解释。无论以何种外形出现,朱雀都是上天的信使,将朱墨书写的信息传递给人类的精英,即有着非凡功业与力量的圣人和统治者。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的传达方式。它是真正的火鸟,体内蕴藏着太阳神圣的能量。有一部古代道教经典写道:“朱雀火之化”,并认为它是太阳鸟,通常化身为“赤乌”:
赫赫赤乌,
惟日之精;
朱羽丹质,
希代而生。
公元776年,一只这样的神鸟曾降临人间,印证了唐代宗的英明统治。
正如刘禹锡所说,这种天使般的红色动物也是热带火热之地的精灵。仰望着赤帝居住的衡山,诗人想像此山“上拂朱鸟翮”。在代表五个方位的鸟类中,朱雀最为不凡。北方的玄鸟,西方的白鹭,东方的苍鹰,以及中间的黄鸟都是后来人为添加的,不具备这种南方神鸟的鲜明个性。
在唐代,红色的热带鸟类被视作真正的神物,南方的首领与王公贵族会将它们进献给宫廷。有时,红色的飞禽也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京都的城门上,在人们眼中,它们便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我们可能会问,什幺样的鸟儿被赋予如此神圣的意义?它来自南方还是北方?这些栖息在长安宫殿梁木上的红色鸟儿很可能是北方鸟类,也许就是一只来自内蒙古森林的红麻料或交喙鸟。这些北方鸟类体型全都不大,也不够显眼,但当时的传说也并未在这些方面有什幺要求。在南方当地所见或进献到北方宫廷的鸟类中,热带森林的野生鸟类、孔雀、甚至石鸡,通常都被或多或少地视作神鸟;火背鷳可能也在其中。然而,这些大型的野生飞禽都与朱雀的颜色不相吻合,倒是某些南越的小型鸟类与朱雀一样,有着美丽的深红色羽毛,比如叉尾太阳鸟、红胸啄花鸟、赤红山椒鸟,这些迷人的觅食者都生活在热带林间或园林的开花植物与灌木丛之中。
然而,儘管中古时期有不少南越鸟类受人关注,但却没有哪一种曾得到过汉人神圣的封号。咬鹃和小太阳鸟都默默无闻;鹦鹉仅仅是一种珍奇之鸟;雉鸡及其同类,只是为宫廷製造盔甲与羽饰提供了实用的羽毛。偶尔有些鸟儿扮演了神圣的角色,但都为时不久。象徵祥瑞的古典的朱雀成了一种纯粹而神秘的符号,不会固定地属于任何一种在五岭与南海之间翱翔的鸟类。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红红绿绿的鹦鹉或咬鹃是理想的朱雀化身,因为它们呈现了南方森林的绿色背景,同时也带来了热带花卉的异国情调。人们甚至可能会想像它飞向中国之外,或在中国之外重生,化身为摩鹿加群岛樱桃红的吸蜜鹦鹉,或是瓜地马拉迷人的绿咬鹃。红鸲鹟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典型,它飞翔在加州的科罗拉多沙漠、亚利桑那,以及墨西哥和南美洲乾旱的土地之上:
它像一道火焰,冲进了潮水般的金色阳光里,飞到了离地面一百英尺的地方。随后,它鲜红的羽冠舒展着,如轻骑兵向后飘扬的头巾一般,并扑扇着震颤的翅膀,轻轻地飘落下来。
实际上,我们能在美国艺术家莫里斯·格拉夫斯的一幅画作中看到朱雀的混合形象,他的绘画题材多为中国的动植物和手工艺品。《鸟精灵》描绘了一只蓝眼、三足的鸟儿,不辨种类,很像三足的赤乌,笼罩在一片红色的结晶或灵气之中。正是这种多样性的表现,使得朱雀在今天成为一种神奇而广义的象徵。
我们儘管对朱雀缺乏特定而具体的形象认知,但仍然可以追问一下:这一古老的象徵在唐代扮演的是什幺角色?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想,还是旧有的观念?特别是,它是否体现了人们的一种愿望--在南越有可能开始新的体验,获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朱雀只是一种挣脱束缚的意象,它闪光的翅膀象徵着从危险境地逃离的力量?又或是唐代人在它那艳丽的色泽中,看到了比凡人身体更加完美的形象,一种自我和灵魂的象徵,能自由地飞翔于未曾探索过的空中花园?
追问这些问题,不只是追问当唐代人想起朱雀这一形象时,他们的脑中会浮现出什幺东西。唐代人可能很少这幺做。这幺追问,更是为了把握唐人对南越感受的总体特徵。这也是为了探寻在来自温带的汉人的想像和渴望中,中古时期的这个朱雀之国究竟是什幺样子的,以及在他们的文学中,朱雀之国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外来者试图在其炎热的庭院中种植家乡的花草,或者在竹子搭建的书斋中,对着笼中的百灵或白颊鸟微笑。也许他们大部分人都不曾有过这样温暖的回忆,而只能在诗中,为远离了这些远在故乡的日常物品而痛心。必然只有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南越鸟类和花卉的独特价值,而大部分人则更关心他们所失去的,而不是关心有可能发现的事物。
北方的诗歌朴素而粗犷;它颤抖着,伴着刺骨的霜冻,大漠的寒风,朦胧的月色以及草原上的积雪。这个真正属于汉人的世界,严厉、冷静而又正统。但也存在另一种古老的审美传统,欣赏温和、温暖、五彩缤纷的长江流域,但这只为汉人了解更南的南方做了部分的铺垫。对被流放南越的汉人来说,他所面对的几乎是全然不同的世界。他会睁大眼睛,盯着各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譬如在高高的树冠下飞翔的巨大的黄盔噪犀鸟,或是从船上飞掠而过的飞鱼。他已经远离了他曾经生活的那片天地,远离了周边的黄土地和桦树、住帐篷的牧民和驼队,远离了周围格局对称的城市和整洁的农田。高山和海洋将他与家人、朋友、平凡的生计阻隔开来,最重要的是,还使他远离了那些早被可敬的传统所神化、被无数宝贵的文献所强化的人物与意象。中古时期南越文献的常见主题,是恐惧、刺激、财富、腐败、中毒、神秘、魔力和幻象等主题,并通过瘴气、蛮人、异域珍宝和鬼怪出没的森林等刻板形象表现出来。鲜明的印象,艳丽的色彩,已经成为某些游客行记的标誌,但大部分人在思考这片新土地时,还只能使用陈词滥调。
面对南越的洞穴和蛮人,许多北方来的官员都怀有强烈的殖民者心态。他们务实而且现实,甚至在作严谨的博物学笔记时,也时时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感。对少数痴迷于南越如画山景的官员来说,总有一些事物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那些冒险的园林家和猎奇者来说,则有另一些事物能吸引他们。
像张九龄那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力也不大。
可能只有一种人会真正欣赏南越的异域特质,他们有敏感的心灵,渴望一种全然不同的完美,而这是辉煌的唐代典範所没有给予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心怀内疚。在中古时代早期,这样的人很少,但在我们当代人中,这种人却有不少,他们品尝了雨林边缘怪异的水果之后:
有时停靠在亚洲的某个港口,
象是回到了伊甸园,忘了归路;
品尝异域的水果,体验陌生的感情,
因巨大的莲花而狂喜。
直到唐代灭亡,南越都不曾出现过卢梭、洛蒂和康拉德这样的人。那里的官员、士兵和贬谪的政客更象是特诺奇提特兰的西班牙人,而不是在东京的法国人。
唐代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南方有过如此的看法——阳光之下的天堂,生活着一群神秘而迷人的仙女,她们的耳畔戴着艳丽的木槿花。那儿和塔希题岛或夏威夷一样,能让人忘却平日的烦恼或恐惧。在先唐文学中,诗歌里所写的古老的南方意象,往往有习见的南越背景,充斥着有毒的植物、蜿蜒的虫蛇、人形的猿猴与猴精、赤色的天空、黑色的森林,以及巫术、神秘和困惑。到了唐代,诗人们试图改弦更张,描写荷塘旁边、木兰舟中,慵懒而面色绯红的越女,以及雾中的神女,只有一部分获得成功。直到九世纪末、十世纪初,随着唐帝国的瓦解,一种新的综合体才成为可能,它介于楚辞所开创的乐观浪漫主义和柳宗元、张九龄等人的自然主义审美之间。当北方人发现与世隔绝的南越也可能有其优点之处,这种改变就产生了,而事实上,他们的父执辈和同辈早已领略过这些优点。于是突然间,南方不再是炼狱或魔窟,而成了神圣的避难所。这个省份从此有了一种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浪漫氛围,展现在李珣和欧阳炯那令人久久难忘的诗句之中。旧有的意象直到此时才得以扭转,并被注入新的生命——朱雀化身为红袖飞扬的南越女子。
然而,这种本土的异国情调仅仅是过渡性的,它连线的两端是古老的殖民帝国与最终多姿多彩的文学舞台。全新的地域、居民、语词所带来的全新体验,能够及时地转化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全新形象。这片热带的伊甸园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部分地化作现实,但它依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崭新的比喻和精神画面,流向北方,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这些满身尘土并且保守的陆地居民,但他一直不停地转变,直到能够接受任何形式的世界,能够接受每一种希罕的经验。
朱雀,作为一种虚构的意象,虽然一直被加于新南方(无论这南方指的是哪里)身上,但却从未完整地存在过。这只东方的火鸟,是柳宗元眼中理想的飞鸟,它静静地筑巢于张九龄的心中,精确而亮丽地呈现于李珣新浪漫的词作中,它只能泛泛地、抽象地,存活于唐代以后的语言和文学作品里。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