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屿之歌清泉故事
《兰屿之歌清泉故事》一书记录了美籍作家丁松青在兰屿、清泉两地的生活故事、心灵随笔。该书为三毛译作,内地首次出版。书中收录了两篇三毛推荐文和五十幅作者珍贵摄影作品。
基本介绍
- 书名:兰屿之歌清泉故事
- 作者:[美] 丁松青
- 译者:三毛
- ISBN:9787530214701
- 类别:文学随笔
- 页数:376
- 定价:39.50
-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5-6
- 装帧:平装
- 品牌: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三毛译作 大陆首度出版
一九六九年丁松青来到台湾,两年后在东南海岸的小岛兰屿做见习修士,与雅美族人度过了难忘的一年。一九七六年夏,在新竹山区的清泉天主堂任职神父,融入泰雅族人的生活,至今仍生活在那里。本书即是丁松青记录下的在兰屿、清泉两地的生活故事、心灵成长。
海岛,飞鱼,木刻小船;青山,吊桥,红砖小屋。
呼唤飞鱼的讚美歌声绕过海岸,白茫茫的山岚覆盖群山间的村落。人人相识,没有秘密。他悄悄走入这天地,走进热情又含蓄的人群,触摸他们质朴的灵魂,共享欢乐与痛苦。
“我不晓得这是否由于我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访客的缘故,总之,每次到了那儿我就禁不住想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它。”
《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是着名作家三毛生前译作,是其挚友丁松青所着,书中详细记录了作者在台湾的兰屿、清泉两地和当地居民交往如歌的行板一般的生活经历和心灵成长故事。全书另附五十幅作者珍贵摄影作品,加上三毛素淡清丽的翻译,《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犹如一对心灵知己共同谱写的人物山水画。在三毛眼中,丁松青 “是诗人,是艺术家,是神父,是可爱之人”, 更是毕生挚友。1969年,23岁的美国人丁松青来到台湾东南海岸的兰屿小岛和清泉村庄生活,三毛眼中的丁松青 “欢喜得十分真纯,这样的一个人,再複杂的俗事,经过他也过滤得明净清澈”。《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既描写了兰屿和清泉当地原始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也描写了现代文化影响下的当地年轻人的内心冲突,随处可见有独到的感悟。当年也是因为三毛的推荐,《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才得以出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的出版还得益于三毛的大力引荐。有感于丁松青和他笔下那些有血有肉的原住民的故事,三毛还亲自带出版社经理专程到深山拜访丁松青签下出版契约,三毛盛讚 “这是一部有生命,有爱心,有无奈,有幽默,又写得至情至性的好文。丁松青那诚实而细腻的笔调,和对当地雅美族同胞真挚的爱,使得兰屿,在他的笔下,在他的心里,成立永恆之岛。” 因对爱与生命相似的心灵感悟,三毛以感性轻灵的文字翻译了挚友丁松青的《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以此将爱与希望传达给更多的人。
作者简介
丁松青,一九四五年生于美国圣地亚哥,九岁时便立志做神父,十八岁进入耶稣会修道院修习。

一九六九年来到台湾,两年后在东南海岸的小岛兰屿做见习修士,与雅美族人度过了难忘的一年。一九七六年夏,自菲律宾修习两年神学后,再次回到台湾,在新竹山区的清泉天主堂任职神父,融入泰雅族人的生活,至今仍生活在那里。
一九七二年,与三毛在兰屿岛上偶然相识,由此开始了两人长达二十年的友谊。在三毛眼中,丁松青不仅是毕生的挚友,更“是诗人,是艺术家,是神父,是可爱之人,是天父的孩子”。
因着对爱与生命相似的心灵感悟,三毛以感性轻灵的文字翻译了他所写下的系列作品《兰屿之歌》《清泉故事》《剎那时光》,将爱与希望传达给更多的人。
作品目录
【兰屿之歌】
有这幺一个人 三毛
和海一起
兰屿
伊莉莎白
礼物
海底世界
自由之歌
岩石
龙眼
拜拜
约玛姑妈
卡吐西
颱风
金项鍊
海夜
里帕沙的心愿
晨光中的儿童
小雅由
田螺与小米
学校
远足
被鬼抓到了
生活点滴
依凡瑞奴之夜
猎猪记
第一艘船
道多陀的世界
肥皂
巴阳
烦恼
打工
黑糖
木屋
迷人的村落
飞鱼
捕鱼
生命之歌
最后的战争
老颜
岁月人生
耕耘与收穫
船的日子
后记
【清泉故事】
清泉之旅 三毛
和山一起
前言
山地世界
风雨故人
半个婚礼
河里的孩子
十只小鸡
运动会
中兴之歌
大丁神父访清泉
耶诞节的泪水
一场大火
演出问题
两个山地人
根
给库诺西的十字架
到更高的山上去
山青会
四种人生
木材工厂
动物的故事
山地舞
安全之旅
鸭毛
施与受
吃飞鼠肉
阿秋的世界
我的姑丈
蛇的故事
山修士
耶诞马槽
部分章节


有这幺一个人
——记丁松青神父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架小飞机在着陆的时候是顺风落地的。当然我关在机舱里并不可能晓得。
我们好似要吹到海水里去了,飞机才悠然止住。
地面上的人迎了过来,笑着对机师说:“今天怎幺如此降落呢?”机师说:“天气好得那个样子,没有危险的!”
一群人上来帮忙下行李,我提出了简单的小背包,对着机场检查官员笑了笑。这儿的人与本岛台湾的,在态度上便是不同,那份从容谦和给人的感觉便是舒坦。
机场边的办公室是水泥的长方房子,立在海边全绿的草坪上,乍见这片景色和人,那份除了安宁之外的寂静,夹着海水、青草地还有机油的味道,丝丝刻骨,这份巨大的震撼却是面对一个全绿的岛屿时所带给我的。
那是十一年前兰屿的一个夏日。
在赴兰屿之前,我已跑过了大半个地球,可是这儿不同,这儿的荒美尚是一片处女地,大地的本身没有太多的人去践踏它,它的风貌也就寂然。
女友子卿与我搭上一辆铁牛车跑到预定的兰屿别馆去,在那个岛上**的旅社里安置了简单的行李。
放下了衣物,急着跑出门去,满腔的欢喜和青春,经过花莲、台东一路的旅行,在初抵这片土地时已到了**,恨不能将自己泼了出去,化做大洪水,浸透这个陌生地,将它溶进生命还是觉得不够。那时候的我,是怎幺样地年轻啊!
景色的美丽事实上是拿它无可奈何的,即使全身所有的心怀意念全都张开了迎接它,而不长期生活在它里面,不做些日常的琐事,不跟天地在个人的起居作息上融合一体,那幺所谓游客似的看山看景,于我还是空洞。
看了一会儿兰屿的山海,我便觉得有些无聊,禁不住想去跟当地的居民做做朋友了。
远远的山坡上立着一些凉亭,山坡与地面接近的地方有着本地人低矮的住宅,沿着上坡一条小径的***一座天主教堂在一片绿色中十分优美地站着。
子卿和我不约而同地指着那个教堂,说走便走,沿着在当时尚有小紫花开满的斜坡爬上去。
那时候去岛上的陌生人有限,我们走路的时候,身边很快引来了一大群小孩子,我随身的布包里放满了台东买去的糖果和吉祥牌香菸。本是不怀好意,预备拿来交换兰屿手刻小木船用的。结果要糖的孩子太热烈,我又是个不忍拒绝孩子的软手人,一路上教堂,一路努力分辨孩子的小脸,给过的绝不再给重複,这幺爬到半路,糖果光了,孩子们也散了。
教堂的面前一个泥巴地的小广场,淙淙的山泉用管子引了下来,不间断地流着。一个妇人蹲在那儿洗两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四周寂静无声,也看不到其他的人。
女友子卿是世上*合适的游伴,她很少跟我黏在一起,是个不多话又自有主张的好朋友。当我低头去喝泉水,跟那妇人说话时,子卿已经自去四处行走了。
我试着抱起那个小女孩,亲亲她美丽的面颊,她的母亲便说:“给你好不好,你给我带去台湾,要不要?”
我听了吓了一跳,微笑着赶快放下孩子,跑到教堂的大门边去。
教堂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严,主人不在,不敢贸然,趴在门缝里偷看内部的情形,这一张望喜得愣了过去。
内部的圣堂墙上大幅的壁画,画着兰屿服装的同胞,戴着他们状如锅盖似的大帽子,手中捧着土地里生长的收穫,活活泼泼地在向神献上感恩。这幺一座神民交融的美图,竟然藏在如此一个小岛上,又是谁的手笔呢?
可惜门缝里张望所见的角度总觉不够,我又是个酷爱美术的人,在这种理由下,便想扭开教堂松松拴着的锁,私自跑进去看个够。
便在动手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后有人,我尚喊了一声:“阿卿,我们想法子进去看画!”猛一回头髮觉身后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的棕发青年。我因自己正在闯教堂,巧被捉个正着,立即飞红了脸,一句想也没有想的话脱口而出:“您是义大利神父吗?”
这完全是大窘之下掩饰自己不良行为的话语。
眼前的青年不算太高的个子,头髮剪得规规矩矩,牙齿极整齐,眼神温柔友善,算得上英俊,一身舒适清洁的旧衣,脚上一双凉鞋,很羞涩,极纯净,脖上一条粗链子挂着一个十字架,没有言语,只是站在我面前。
他不说什幺,可是透露的身体语言便明白告诉了我,这个青年,是有光辉,有信仰的,并且不是个义大利人。刚才那句问话真是莫名其妙。
这一回,是他开了门,谦卑和气又安详地将子卿与我引进了圣堂。
教堂在广场的正面,左厢另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放着一个医药柜,另外挤着一架老风琴,我试按了几个音,有些琴键下去了便不肯再跳起来,半哑的。
——记丁松青神父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架小飞机在着陆的时候是顺风落地的。当然我关在机舱里并不可能晓得。
我们好似要吹到海水里去了,飞机才悠然止住。
地面上的人迎了过来,笑着对机师说:“今天怎幺如此降落呢?”机师说:“天气好得那个样子,没有危险的!”
一群人上来帮忙下行李,我提出了简单的小背包,对着机场检查官员笑了笑。这儿的人与本岛台湾的,在态度上便是不同,那份从容谦和给人的感觉便是舒坦。
机场边的办公室是水泥的长方房子,立在海边全绿的草坪上,乍见这片景色和人,那份除了安宁之外的寂静,夹着海水、青草地还有机油的味道,丝丝刻骨,这份巨大的震撼却是面对一个全绿的岛屿时所带给我的。
那是十一年前兰屿的一个夏日。
在赴兰屿之前,我已跑过了大半个地球,可是这儿不同,这儿的荒美尚是一片处女地,大地的本身没有太多的人去践踏它,它的风貌也就寂然。
女友子卿与我搭上一辆铁牛车跑到预定的兰屿别馆去,在那个岛上**的旅社里安置了简单的行李。
放下了衣物,急着跑出门去,满腔的欢喜和青春,经过花莲、台东一路的旅行,在初抵这片土地时已到了**,恨不能将自己泼了出去,化做大洪水,浸透这个陌生地,将它溶进生命还是觉得不够。那时候的我,是怎幺样地年轻啊!
景色的美丽事实上是拿它无可奈何的,即使全身所有的心怀意念全都张开了迎接它,而不长期生活在它里面,不做些日常的琐事,不跟天地在个人的起居作息上融合一体,那幺所谓游客似的看山看景,于我还是空洞。
看了一会儿兰屿的山海,我便觉得有些无聊,禁不住想去跟当地的居民做做朋友了。
远远的山坡上立着一些凉亭,山坡与地面接近的地方有着本地人低矮的住宅,沿着上坡一条小径的***一座天主教堂在一片绿色中十分优美地站着。
子卿和我不约而同地指着那个教堂,说走便走,沿着在当时尚有小紫花开满的斜坡爬上去。
那时候去岛上的陌生人有限,我们走路的时候,身边很快引来了一大群小孩子,我随身的布包里放满了台东买去的糖果和吉祥牌香菸。本是不怀好意,预备拿来交换兰屿手刻小木船用的。结果要糖的孩子太热烈,我又是个不忍拒绝孩子的软手人,一路上教堂,一路努力分辨孩子的小脸,给过的绝不再给重複,这幺爬到半路,糖果光了,孩子们也散了。
教堂的面前一个泥巴地的小广场,淙淙的山泉用管子引了下来,不间断地流着。一个妇人蹲在那儿洗两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四周寂静无声,也看不到其他的人。
女友子卿是世上*合适的游伴,她很少跟我黏在一起,是个不多话又自有主张的好朋友。当我低头去喝泉水,跟那妇人说话时,子卿已经自去四处行走了。
我试着抱起那个小女孩,亲亲她美丽的面颊,她的母亲便说:“给你好不好,你给我带去台湾,要不要?”
我听了吓了一跳,微笑着赶快放下孩子,跑到教堂的大门边去。
教堂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严,主人不在,不敢贸然,趴在门缝里偷看内部的情形,这一张望喜得愣了过去。
内部的圣堂墙上大幅的壁画,画着兰屿服装的同胞,戴着他们状如锅盖似的大帽子,手中捧着土地里生长的收穫,活活泼泼地在向神献上感恩。这幺一座神民交融的美图,竟然藏在如此一个小岛上,又是谁的手笔呢?
可惜门缝里张望所见的角度总觉不够,我又是个酷爱美术的人,在这种理由下,便想扭开教堂松松拴着的锁,私自跑进去看个够。
便在动手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后有人,我尚喊了一声:“阿卿,我们想法子进去看画!”猛一回头髮觉身后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的棕发青年。我因自己正在闯教堂,巧被捉个正着,立即飞红了脸,一句想也没有想的话脱口而出:“您是义大利神父吗?”
这完全是大窘之下掩饰自己不良行为的话语。
眼前的青年不算太高的个子,头髮剪得规规矩矩,牙齿极整齐,眼神温柔友善,算得上英俊,一身舒适清洁的旧衣,脚上一双凉鞋,很羞涩,极纯净,脖上一条粗链子挂着一个十字架,没有言语,只是站在我面前。
他不说什幺,可是透露的身体语言便明白告诉了我,这个青年,是有光辉,有信仰的,并且不是个义大利人。刚才那句问话真是莫名其妙。
这一回,是他开了门,谦卑和气又安详地将子卿与我引进了圣堂。
教堂在广场的正面,左厢另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放着一个医药柜,另外挤着一架老风琴,我试按了几个音,有些琴键下去了便不肯再跳起来,半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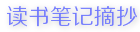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