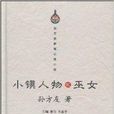
孙方友:小镇人物2 巫女
基本介绍
- 书名:孙方友:小镇人物2 巫女
-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 页数:250页
- 开本:32
- 品牌:凤凰壹力
- 作者:张方友 墨白
- 出版日期:2009年8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807650515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小镇人物2:巫女》是中国当代笔记体小说之王孙方友的作品。
在中国,不提笔记体小说则罢,如果提,则必提孙方友。
短短千字,便可写出一个镇、一座城乃至全中国底层社会的缩影。在各式粗糙的长篇小说泛滥的今天,有这样一扇精緻的视窗,可以让我们欣赏到小镇的万千风情,感受到心灵的丝丝颤动,幸甚!幸甚!
笔记体小说:文体名,笔记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题材广泛。其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称为笔记体小说,亦称笔记小说。代表作有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在中国,不提笔记体小说则罢,如果提,则必提孙方友。
短短千字,便可写出一个镇、一座城乃至全中国底层社会的缩影。在各式粗糙的长篇小说泛滥的今天,有这样一扇精緻的视窗,可以让我们欣赏到小镇的万千风情,感受到心灵的丝丝颤动,幸甚!幸甚!
笔记体小说:文体名,笔记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题材广泛。其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称为笔记体小说,亦称笔记小说。代表作有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作者简介
孙方友,男,1950年生,河南淮阳县新站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创作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三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十余部,电视剧百余集,计五百多万字。代表作有:《虚幻构成》、《谎释》、《陈州笔记》系列、《小镇人物》系列等。有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等国文字。
图书目录
1994年
小镇上的大人物
麻嫂
李小济
于老六
黄国棋
狗拽
孙多贤
飘飘
保镖西岸
袁三
1995年
欢欢
歌歌
晶晶
圆圆
尤狗子
流注
香香
老蔫
1996年
老白支书
鞋匠白五
乡长白钢
司机白光
民师白春
乡医刘山
乡师白芳
巫女
打工妹菊
打工妹兰
欣欣
安主任
马仁秀
钱县长
1997年
河边错误
老马
老典
罗锅
1998年
老梅
老曾
老常
老伊
袁板胡
老横
雷二少
方鑒堂
滢滢
苗苗
郭先生
老牛
戴先生
宝德
老金
王财
附录 我的大哥孙方友
小镇上的大人物
麻嫂
李小济
于老六
黄国棋
狗拽
孙多贤
飘飘
保镖西岸
袁三
1995年
欢欢
歌歌
晶晶
圆圆
尤狗子
流注
香香
老蔫
1996年
老白支书
鞋匠白五
乡长白钢
司机白光
民师白春
乡医刘山
乡师白芳
巫女
打工妹菊
打工妹兰
欣欣
安主任
马仁秀
钱县长
1997年
河边错误
老马
老典
罗锅
1998年
老梅
老曾
老常
老伊
袁板胡
老横
雷二少
方鑒堂
滢滢
苗苗
郭先生
老牛
戴先生
宝德
老金
王财
附录 我的大哥孙方友
文摘
1994年
小镇上的大人物
大人物姓柳,名侃,字澜波。众人只知他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至于官至何位,没多少人能说清。据传当年北京和平解放时,他曾做过国军代表,可事成之后,他却坚持“一臣不保二主”,弃甲归田,隐居乡里,清享晚年。
论辈分,他在镇东街是首屈一指的,我应该喊他为“爷”。那年月,他那身份令人悚然。称呼近了大有勾结“战犯”之嫌,“爷爷”之类万万喊不得。可他满头银丝,一对双眼皮儿夹杂着几根红丝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总能威逼着晚辈人喊他一声“老侃”。
记得第一次拉他游街的时候,他很顺从。“造反派”把纸牌子摊在他面前,让他自个儿写。他毫不迟疑,挥笔而就:“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官——柳侃”。字型遒劲,且又是怀素体。不料笔未放稳,头颅上就挨了一掌。接下来,苍劲有力的“弃暗投明”与“将官”换成了瘦小丑陋的“罪大恶极”和“战犯”,然后套在他的脖子上,一阵高喝,被拉了出去,前面锣鼓开道,后面口号声声。他却依然迈着军人步伐,一点儿不含糊。
接着是搜家。院子里挤满了大人小孩。执行者呵声如雷,他却立正如木。僵持久了,显得无聊,人们便开始观赏小院景色。小院不大,篱笆分道。榕花树、棠梨树、白檀、石榴,奇花异草布满角角落落……突然,一阵高喧,有人拿出了一布包儿。人们簇拥而上,周围的人都伸长了脖颈,踮起了脚跟儿,屏气静声,单等布包儿打开,看到底是否电台手枪之类。随着人们的唏嘘声,执行者从包里掏出了一本影集,掀开一页,晃动一圈儿。第一页是老侃与一个肩扛“门板”、胸佩勋章的光头的合影;第二页是当年北京谈判的集照;第三页便是他与妻子女儿的全家福。照片上的两个女人都是烫髮、旗袍,年轻的那一位还肩披青纱。据讲解人说老侃的妻子是天津一位资本家的女儿,解放初期去世,只留下那位身披青纱的独生女儿,现在天津一个什幺所搞研究。这影集也就成了他的罪证。每掀一页,照片上便出现不少国民党大人物,他的头上就不免被人击几下。他却面若冰霜,一副受训的立正姿态。
每天游斗归来,他照样要把武装带系在衣外,走路仍是军人步伐。早晨坚持跑操,在镇外的官道上来回走动,最后还要在他自製的单槓上起落几下。过了数日,斗争他的人竟怏怏地对他撒手不管了。偷问原因,原来他与北京通了信,一位大人物替他说了话。人们就觉得他神通广大,再不惹他,只让他在队里干些散活计。
开初,他挑尿肥。每天早饭后,就见他挑着尿桶,提着尿勺走东家串西家。太阳落的时候,也是他在颍河边刷尿桶的时候。他刷尿桶极认真,用一个自製的小竹刷,“哗啦啦,哗啦啦”,直把尿桶刷得比人家的水桶还乾净为止。
有一天,他突然不挑尿肥了,也不向队长说,只在家中学“毛选”。各家尿肥满了,反映给队长,队长便去寻他。他淡淡地说:“我上了年纪,挑不动尿肥了,请你另请高明。”队长知道他通“上神”,便派他去看麦子。他放下书,摘下花镜,朝队长点点头。第二天,他拿着苫子、凉蓆、小褥子、小单子、小枕头、小茶壶、小茶盅、大雨伞、长绳子,搬家一样到了地里。他围地转了一圈儿,看了地形,寻到大树下,认真铺了床,然后用绳子把撑开的雨伞吊在上面,仰面正睡,四肢放妥,轻轻打起鼾来。睡足一时,便坐起来学“毛选”。他专看“战争篇”,尤其对战争的电文和有关战争的注解,一点儿也不放过。
夕阳如火的时刻,他开始收拾东西回家做晚饭。他吃饭一直定量,用秤盘小心地称着削了皮的地瓜乾,然后从罐儿里取出两个鸡蛋。他的女儿每月都给他寄钱来。他把钱换成小票,一天花多少就取出多少。有一天,他家突然添了个客人。客人满头银髮,看样子比他岁数还大,那客人来后,他再不下手做饭,就坐在一个竹椅上与那老者闲侃。那老者又烧火又切菜,忙上忙下地做好了,又端到桌子上,取了筷子,再请他入座。那老者住了半个月,认认真真地侍候了他半个月。许久之后,他才说那老者在他手下当过团长。
1985年我参加工作以后,就极少见到老侃了。听家乡人说上头补发了他不少钱,现在照月给他生活费。他那在天津的女儿回来过一次。那女人已年过半百,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玉照上的倩影了。海峡两岸活络以后,从那边回来的人不断朝他那儿跑,来了,就做饭,给他端吃端喝……
前年夏,我回乡探亲,再次见到了老侃。他已年过九旬,但身板儿还算硬朗。麦忙五月天,他却每天都去颍河湾里散步,然后寻到一处,一坐一个上午。
有一天,我去颍河里洗澡,离老远就见老侃坐在河坡上。我好奇地游过去,他竟没发现我,双目痴呆地盯着什幺。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下惊诧得张大了嘴巴。一块硕大的骨头上,爬满了黑色黄色的蚂蚁。“黑军”和“黄军”为争夺那块骨头,正进行着殊死搏斗。成千上万的蚂蚁,组成了黑黄两个“军团”,浩浩蕩蕩,前赴后继,那场面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一年之后,老侃患脑溢血离世,他死的时候已不能说话,只一个劲儿地指桌子。他的女儿拉开抽屉,找出一份提前立好的遗嘱。遗嘱上安排不让女儿为他披麻戴孝送纸钱,只要求女儿每年清明节上坟之时,在他的坟头上放一块骨头……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遗嘱!
此地离天津两千华里,他的女儿也已年迈,决不会每年都回来。可令人不解的是,老侃的坟头上却不断有人放骨头,招来成千上万的蚂蚁为骨头而战。
谁放的?不知道!
麻嫂
麻嫂并不麻。听人说,麻嫂年轻时长得很漂亮。
麻嫂也不姓麻,只因她的丈夫姓麻,所以众人都称她为麻嫂。麻嫂很不喜欢麻哥的姓氏,常常说:“多好一个人儿,被你们这鸟姓生生拉下不少分儿!知道的说我长得还可以,不知道的还以为俺是个麻脸哩!你们要是姓美多好,人家一喊美嫂,那感觉立刻就不一样!”
麻嫂姓田,娘家住在紧靠颍河的田家大湾村。由于田家人老几辈都是渔民,所以麻嫂从小就会打鱼。小时候,她整天在河里野,胆大心细。有一天午后她去河坡里割芦苇,突然发现一个大老鳖正在河滩上晒盖,就飞似的跑上去,踩在了老鳖身上。那老鳖有簸箩般大,驮着她就朝水里跑。麻嫂急中生智,挥起镰刀削断了鳖爪,等鳖爬不动了,她也浑身像个血人儿了。后来父亲来了,帮她把鳖弄到家,剥出了不少珍珠。麻嫂的母亲急忙趁热把珍珠用线串了起来,因为珍珠为奇物,一凉就串不成,而串不成线的珍珠至少要少卖一半钱。后来父亲卖了那串珍珠,给麻嫂扯了一身花布料。麻嫂捨不得穿,锁进了箱子里。镇里一位郎中听说田家湾出了一个奇鳖,要求买走那鳖盖,可麻嫂执意不卖,说是留个纪念。她用小刀把鳖盖刮净,又用水洗了几遍,然后对爹说:“咱家穷,让它给我当陪嫁吧!”后来麻哥娶麻嫂的时候,嫁妆里果然就有这个大鳖盖。那鳖盖奇大,挂了红绸,招来不少人看稀罕。乡入见麻嫂长得好,都说麻哥娶了个老鳖精,小心生一窝儿小鳖娃儿。麻哥就觉得晦气,对麻嫂说:“弄这个盖盖子乾什幺?”麻嫂白了一眼麻哥,说:“你懂个屁!鳖为宝物,等我们有了娃儿,把他放在鳖盖里睡觉,清凉润肺,再热的天也不上火!”
麻嫂的嫁妆中,还有一样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鱼皮鞋。鱼皮为草鱼皮。此地人称这种鱼为“火头”。这种鱼皮又厚又结实,不但能制胡琴,还能做鞋。鱼皮鞋不过水不过潮,踏雪不沾雪。那时候农家穷,谁能买得起胶鞋,麻嫂的娘只得用这种鱼皮做鞋让女儿踏泥踩水度雨天。
有一日,麻嫂穿着鱼皮鞋披着蓑衣跟父亲去河里取钩。一到河边,发现鱼钩被拽断了大半。她和父亲急忙划船顺水寻找,原来是钩住了一个罕见的大鱼。那鱼足有六尺长,一百来斤。父亲把大鱼撂到了岸上。眼见那鱼又要朝水里跃,麻嫂一个箭步飞上岸,用刀一下划开了鱼肚。鱼肚一开,不想从里边滚出一只娃娃的胳膊。那胳膊又白又嫩,手脖儿上还繫着一个带铃的银镯子。麻嫂一见直吓得面色苍白,又呕又吐,从此再不吃鱼。
由于麻嫂不吃鱼了,嫁到镇上后,就再不打鱼。只是麻嫂一生喜水,又划一手好船,便和麻哥在码头上边开了个小渡口,单赚那些等不及大渡船的人的小钱。一天到晚,从此岸到彼岸,也能搞个六块七块的。没想好景不长,码头上的大渡船全装上了机器,速度快了几多倍,码头上再也存不住人。加上小渡船危险又缓慢,就更少有渡客光顾麻嫂了。麻嫂很无奈,最后只得撤了渡口,回家种地了。
那一年,麻嫂二十六岁。那时候麻嫂已为麻哥生下了一儿一女。一儿一女从小睡在那个大鳖盖里,仿佛都沾了灵气,上学读书如喝书,眼下双双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由于光靠土地收入,供养两个高中生就有些窘迫。万般无奈,麻嫂就决定卖掉那只大鳖盖。当年要买那只大鳖盖的郎中还活着,麻嫂找到他说明了心意。老郎中为人耿直,对麻嫂说:“这些年吃鳖的多,鳖越来越金贵,鳖甲也值钱。你那鳖盖足有二十斤,一般人买不起了,不如到地区大药堂里问一问。”麻嫂见老先生实在,很是感动,忙派麻哥去了地区中药堂。地区中药堂很公正,说是麻嫂当年逮的那只大鳖为千年老鳖,属珍贵中药,一下出钱七乾元,敲锣打鼓地运走了。
麻嫂手拿一捆儿钞票,怅然望着远去的迎鳖甲队伍,心里好失落!
为死钱活用,麻嫂让麻哥请人修补了那只破船,置买了渔具,又开始下河捕鱼了。
不知为什幺,麻嫂对鳖就产生了某种複杂的情愫。每每捕到鳖,她再也捨不得吃捨不得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水池,把鳖养了起来,然后去河滩里拉来沙子,在水池边铺了。麻嫂对麻哥说:“鳖对咱家有恩,咱一定要好生待它们!鳖喜阴又喜阳,它们在沙滩上晒盖的时候,都不要惊动它们!”
小镇上的大人物
大人物姓柳,名侃,字澜波。众人只知他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至于官至何位,没多少人能说清。据传当年北京和平解放时,他曾做过国军代表,可事成之后,他却坚持“一臣不保二主”,弃甲归田,隐居乡里,清享晚年。
论辈分,他在镇东街是首屈一指的,我应该喊他为“爷”。那年月,他那身份令人悚然。称呼近了大有勾结“战犯”之嫌,“爷爷”之类万万喊不得。可他满头银丝,一对双眼皮儿夹杂着几根红丝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总能威逼着晚辈人喊他一声“老侃”。
记得第一次拉他游街的时候,他很顺从。“造反派”把纸牌子摊在他面前,让他自个儿写。他毫不迟疑,挥笔而就:“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官——柳侃”。字型遒劲,且又是怀素体。不料笔未放稳,头颅上就挨了一掌。接下来,苍劲有力的“弃暗投明”与“将官”换成了瘦小丑陋的“罪大恶极”和“战犯”,然后套在他的脖子上,一阵高喝,被拉了出去,前面锣鼓开道,后面口号声声。他却依然迈着军人步伐,一点儿不含糊。
接着是搜家。院子里挤满了大人小孩。执行者呵声如雷,他却立正如木。僵持久了,显得无聊,人们便开始观赏小院景色。小院不大,篱笆分道。榕花树、棠梨树、白檀、石榴,奇花异草布满角角落落……突然,一阵高喧,有人拿出了一布包儿。人们簇拥而上,周围的人都伸长了脖颈,踮起了脚跟儿,屏气静声,单等布包儿打开,看到底是否电台手枪之类。随着人们的唏嘘声,执行者从包里掏出了一本影集,掀开一页,晃动一圈儿。第一页是老侃与一个肩扛“门板”、胸佩勋章的光头的合影;第二页是当年北京谈判的集照;第三页便是他与妻子女儿的全家福。照片上的两个女人都是烫髮、旗袍,年轻的那一位还肩披青纱。据讲解人说老侃的妻子是天津一位资本家的女儿,解放初期去世,只留下那位身披青纱的独生女儿,现在天津一个什幺所搞研究。这影集也就成了他的罪证。每掀一页,照片上便出现不少国民党大人物,他的头上就不免被人击几下。他却面若冰霜,一副受训的立正姿态。
每天游斗归来,他照样要把武装带系在衣外,走路仍是军人步伐。早晨坚持跑操,在镇外的官道上来回走动,最后还要在他自製的单槓上起落几下。过了数日,斗争他的人竟怏怏地对他撒手不管了。偷问原因,原来他与北京通了信,一位大人物替他说了话。人们就觉得他神通广大,再不惹他,只让他在队里干些散活计。
开初,他挑尿肥。每天早饭后,就见他挑着尿桶,提着尿勺走东家串西家。太阳落的时候,也是他在颍河边刷尿桶的时候。他刷尿桶极认真,用一个自製的小竹刷,“哗啦啦,哗啦啦”,直把尿桶刷得比人家的水桶还乾净为止。
有一天,他突然不挑尿肥了,也不向队长说,只在家中学“毛选”。各家尿肥满了,反映给队长,队长便去寻他。他淡淡地说:“我上了年纪,挑不动尿肥了,请你另请高明。”队长知道他通“上神”,便派他去看麦子。他放下书,摘下花镜,朝队长点点头。第二天,他拿着苫子、凉蓆、小褥子、小单子、小枕头、小茶壶、小茶盅、大雨伞、长绳子,搬家一样到了地里。他围地转了一圈儿,看了地形,寻到大树下,认真铺了床,然后用绳子把撑开的雨伞吊在上面,仰面正睡,四肢放妥,轻轻打起鼾来。睡足一时,便坐起来学“毛选”。他专看“战争篇”,尤其对战争的电文和有关战争的注解,一点儿也不放过。
夕阳如火的时刻,他开始收拾东西回家做晚饭。他吃饭一直定量,用秤盘小心地称着削了皮的地瓜乾,然后从罐儿里取出两个鸡蛋。他的女儿每月都给他寄钱来。他把钱换成小票,一天花多少就取出多少。有一天,他家突然添了个客人。客人满头银髮,看样子比他岁数还大,那客人来后,他再不下手做饭,就坐在一个竹椅上与那老者闲侃。那老者又烧火又切菜,忙上忙下地做好了,又端到桌子上,取了筷子,再请他入座。那老者住了半个月,认认真真地侍候了他半个月。许久之后,他才说那老者在他手下当过团长。
1985年我参加工作以后,就极少见到老侃了。听家乡人说上头补发了他不少钱,现在照月给他生活费。他那在天津的女儿回来过一次。那女人已年过半百,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玉照上的倩影了。海峡两岸活络以后,从那边回来的人不断朝他那儿跑,来了,就做饭,给他端吃端喝……
前年夏,我回乡探亲,再次见到了老侃。他已年过九旬,但身板儿还算硬朗。麦忙五月天,他却每天都去颍河湾里散步,然后寻到一处,一坐一个上午。
有一天,我去颍河里洗澡,离老远就见老侃坐在河坡上。我好奇地游过去,他竟没发现我,双目痴呆地盯着什幺。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下惊诧得张大了嘴巴。一块硕大的骨头上,爬满了黑色黄色的蚂蚁。“黑军”和“黄军”为争夺那块骨头,正进行着殊死搏斗。成千上万的蚂蚁,组成了黑黄两个“军团”,浩浩蕩蕩,前赴后继,那场面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一年之后,老侃患脑溢血离世,他死的时候已不能说话,只一个劲儿地指桌子。他的女儿拉开抽屉,找出一份提前立好的遗嘱。遗嘱上安排不让女儿为他披麻戴孝送纸钱,只要求女儿每年清明节上坟之时,在他的坟头上放一块骨头……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遗嘱!
此地离天津两千华里,他的女儿也已年迈,决不会每年都回来。可令人不解的是,老侃的坟头上却不断有人放骨头,招来成千上万的蚂蚁为骨头而战。
谁放的?不知道!
麻嫂
麻嫂并不麻。听人说,麻嫂年轻时长得很漂亮。
麻嫂也不姓麻,只因她的丈夫姓麻,所以众人都称她为麻嫂。麻嫂很不喜欢麻哥的姓氏,常常说:“多好一个人儿,被你们这鸟姓生生拉下不少分儿!知道的说我长得还可以,不知道的还以为俺是个麻脸哩!你们要是姓美多好,人家一喊美嫂,那感觉立刻就不一样!”
麻嫂姓田,娘家住在紧靠颍河的田家大湾村。由于田家人老几辈都是渔民,所以麻嫂从小就会打鱼。小时候,她整天在河里野,胆大心细。有一天午后她去河坡里割芦苇,突然发现一个大老鳖正在河滩上晒盖,就飞似的跑上去,踩在了老鳖身上。那老鳖有簸箩般大,驮着她就朝水里跑。麻嫂急中生智,挥起镰刀削断了鳖爪,等鳖爬不动了,她也浑身像个血人儿了。后来父亲来了,帮她把鳖弄到家,剥出了不少珍珠。麻嫂的母亲急忙趁热把珍珠用线串了起来,因为珍珠为奇物,一凉就串不成,而串不成线的珍珠至少要少卖一半钱。后来父亲卖了那串珍珠,给麻嫂扯了一身花布料。麻嫂捨不得穿,锁进了箱子里。镇里一位郎中听说田家湾出了一个奇鳖,要求买走那鳖盖,可麻嫂执意不卖,说是留个纪念。她用小刀把鳖盖刮净,又用水洗了几遍,然后对爹说:“咱家穷,让它给我当陪嫁吧!”后来麻哥娶麻嫂的时候,嫁妆里果然就有这个大鳖盖。那鳖盖奇大,挂了红绸,招来不少人看稀罕。乡入见麻嫂长得好,都说麻哥娶了个老鳖精,小心生一窝儿小鳖娃儿。麻哥就觉得晦气,对麻嫂说:“弄这个盖盖子乾什幺?”麻嫂白了一眼麻哥,说:“你懂个屁!鳖为宝物,等我们有了娃儿,把他放在鳖盖里睡觉,清凉润肺,再热的天也不上火!”
麻嫂的嫁妆中,还有一样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鱼皮鞋。鱼皮为草鱼皮。此地人称这种鱼为“火头”。这种鱼皮又厚又结实,不但能制胡琴,还能做鞋。鱼皮鞋不过水不过潮,踏雪不沾雪。那时候农家穷,谁能买得起胶鞋,麻嫂的娘只得用这种鱼皮做鞋让女儿踏泥踩水度雨天。
有一日,麻嫂穿着鱼皮鞋披着蓑衣跟父亲去河里取钩。一到河边,发现鱼钩被拽断了大半。她和父亲急忙划船顺水寻找,原来是钩住了一个罕见的大鱼。那鱼足有六尺长,一百来斤。父亲把大鱼撂到了岸上。眼见那鱼又要朝水里跃,麻嫂一个箭步飞上岸,用刀一下划开了鱼肚。鱼肚一开,不想从里边滚出一只娃娃的胳膊。那胳膊又白又嫩,手脖儿上还繫着一个带铃的银镯子。麻嫂一见直吓得面色苍白,又呕又吐,从此再不吃鱼。
由于麻嫂不吃鱼了,嫁到镇上后,就再不打鱼。只是麻嫂一生喜水,又划一手好船,便和麻哥在码头上边开了个小渡口,单赚那些等不及大渡船的人的小钱。一天到晚,从此岸到彼岸,也能搞个六块七块的。没想好景不长,码头上的大渡船全装上了机器,速度快了几多倍,码头上再也存不住人。加上小渡船危险又缓慢,就更少有渡客光顾麻嫂了。麻嫂很无奈,最后只得撤了渡口,回家种地了。
那一年,麻嫂二十六岁。那时候麻嫂已为麻哥生下了一儿一女。一儿一女从小睡在那个大鳖盖里,仿佛都沾了灵气,上学读书如喝书,眼下双双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由于光靠土地收入,供养两个高中生就有些窘迫。万般无奈,麻嫂就决定卖掉那只大鳖盖。当年要买那只大鳖盖的郎中还活着,麻嫂找到他说明了心意。老郎中为人耿直,对麻嫂说:“这些年吃鳖的多,鳖越来越金贵,鳖甲也值钱。你那鳖盖足有二十斤,一般人买不起了,不如到地区大药堂里问一问。”麻嫂见老先生实在,很是感动,忙派麻哥去了地区中药堂。地区中药堂很公正,说是麻嫂当年逮的那只大鳖为千年老鳖,属珍贵中药,一下出钱七乾元,敲锣打鼓地运走了。
麻嫂手拿一捆儿钞票,怅然望着远去的迎鳖甲队伍,心里好失落!
为死钱活用,麻嫂让麻哥请人修补了那只破船,置买了渔具,又开始下河捕鱼了。
不知为什幺,麻嫂对鳖就产生了某种複杂的情愫。每每捕到鳖,她再也捨不得吃捨不得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水池,把鳖养了起来,然后去河滩里拉来沙子,在水池边铺了。麻嫂对麻哥说:“鳖对咱家有恩,咱一定要好生待它们!鳖喜阴又喜阳,它们在沙滩上晒盖的时候,都不要惊动它们!”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