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集:晚饭花集》读后感1700字
这本《晚饭花集》是唐卡未亡送给我的。唐卡又叫小白,她有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妖娆”的老公。女儿叫小杮子,老公叫韦大爷。今年,小杮子慢慢地长大了,会坐在小凳子上玩玩具,嘴里嘀嘀咕咕,她妈妈说:“小杮子,这玩具应该这么玩。”小杮子头也不抬,只顾把玩具摆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在她小小的心眼儿里,做一艘船比做一架飞机有意思多了,什么也做不成比做成点什么也有意思多了。韦大爷呢,韦大爷似乎总是光着膀子在厨房里做饭。乒乒乓乓,一一菜切好了,又乒乒乓乓一一菜烧好了;韦大爷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说:“小杮子,我们叫妞妞吃饭吧。”小杮子连忙放下玩具,小脑袋一回,喊道:“妞妞饭做好了快吃饭呀!”她从来不断句,也不大声,年幼让她的声音甜得跟个水蜜桃似的好听。妞妞是唐卡的小名。
我喜欢这样生活的一家子,正如她送我的这本书里,生活着的那些安静而浅悦的人们。
我当然知道晚饭花的意思。晚饭花在我的印象里叫紫茉莉,或者地雷花。从大门出去,院墙下就生长着很多。这花不能叫养,冬天里光秃秃的一片土地,春天里开始长出芽尖,到夏天就是蓬蓬勃勃的一大丛。比起长叶,紫茉莉也酷爱开花,上一朵,下一朵,左边,右边,一点规律也没有,像大事临头,让谁给手忙脚乱地插了一身。如果把那钟形一样的紫色花朵去掉花柄,紫茉莉似乎有点像柔化了的茑萝。但茑萝是种很爱惜自己的植物,既怕寒冷,又忌霜冻,就连平时站着也得找一点什么来扶持着。藤本植物大都如此,可是又娇滴滴的,由不得人不去喜爱。
这样比起来,紫茉莉枝叶茂密,花朵繁多,连果实都疙疙瘩瘩像绣满了黑社会的纹身,太粗放了,只能算作花中的“女汉子”。
但我还是爱紫茉莉,因为它也爱我。这世上有许多花,与我只一面之缘,而紫茉莉不是,它和我年年有约。它能年年越过贫瘠的冬天把新的生命呈现给我,而且越来越多。汪曾祺说人们讨厌她旺盛的生命力,长得到处都是,连常青藤在她下面都搁不住脚;但人们难道不知道,爱本来就是要这么放肆才好玩么?
因为是多方力荐,《晚饭花集》这本书我看得很谨慎,毕竟汪曾祺有个头衔我很害怕:“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最后”两字总让我觉得悲情,仿佛一脉相承,到这里突然断了。之后我想起沈从文,是不是他只有弟子没徒孙了呢?那多可惜啊。
认真看一遍,汪曾祺的文笔算不错的,清清淡淡,显得极为稳重;偶尔有些妙语,又极有风度。汪曾祺自己也很满意,认为是“有点像是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洋味儿还太少了,像“木板门又关了,把门上的一副春联关在外面。”这样的,通篇没有几句。所以我不厚道地想,汪曾祺还真的是“士大夫”啊。如果用不乖的一句诗来形容他的写作应该比较恰当,虽然不乖这首诗写得非常萧条,一眼看去就是怀念旧情人的。全诗录来是这样子:
夜雨远风辜负久,有时寂寞向谁陈。
爱君点划自成阵,愧我蒿萧难着春。
斯世同怀惟有梦,江湖两忘暂存身。
繁霜侵鬓期于米,词笔如兰益可亲。
这里不说“江湖两忘暂存身”的事,毕竟我们之间还没有好到可以共享一些失败的恋情。然而“词笔如兰益可亲”这句,在我看来,简直是为汪曾祺定做下来的:寂寞如兰,然后可亲;幽深如谷,所以不可昵。
然而汪曾祺是一定不会同意把自己比做兰的。必须赞叹的是,他用了很深的入世之法来写出世之心,以至于贾平凹说他是个“人精”,至于贾平凹,他也有个让我害怕的头衔:“中国最好的散文大师”一一我觉得大多人可能一生都活在这些盛名之下了,而对盛名的主人无法了解。
他们了解汪曾祺其实是这样写的吗?“我对晚饭花这种花并不怎么欣赏……这是一种很低贱的花,比牵牛花、凤仙花以及北京人叫做“死不了”的草花还要低贱。”
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对花木要有分别心。是花低贱,无足珍贵,所以就用来做了一本集子的名字。如果真这么想,那么一个人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他的老师。他的老师从不轻贱自己和他人,在他的《湘行散记》里,记着有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头子,走起路来,拉起船来,骂起人来,是丝毫也不肯让于精壮小伙儿的。一个又老又狡猾的家伙,看着他坐在石头上那数钱的神气,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老师感叹道:那样子,简直是一个托尔斯泰!
“那样子,简直是一个托尔斯泰!”忍不住再读一遍。
池 2017.06.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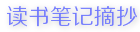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