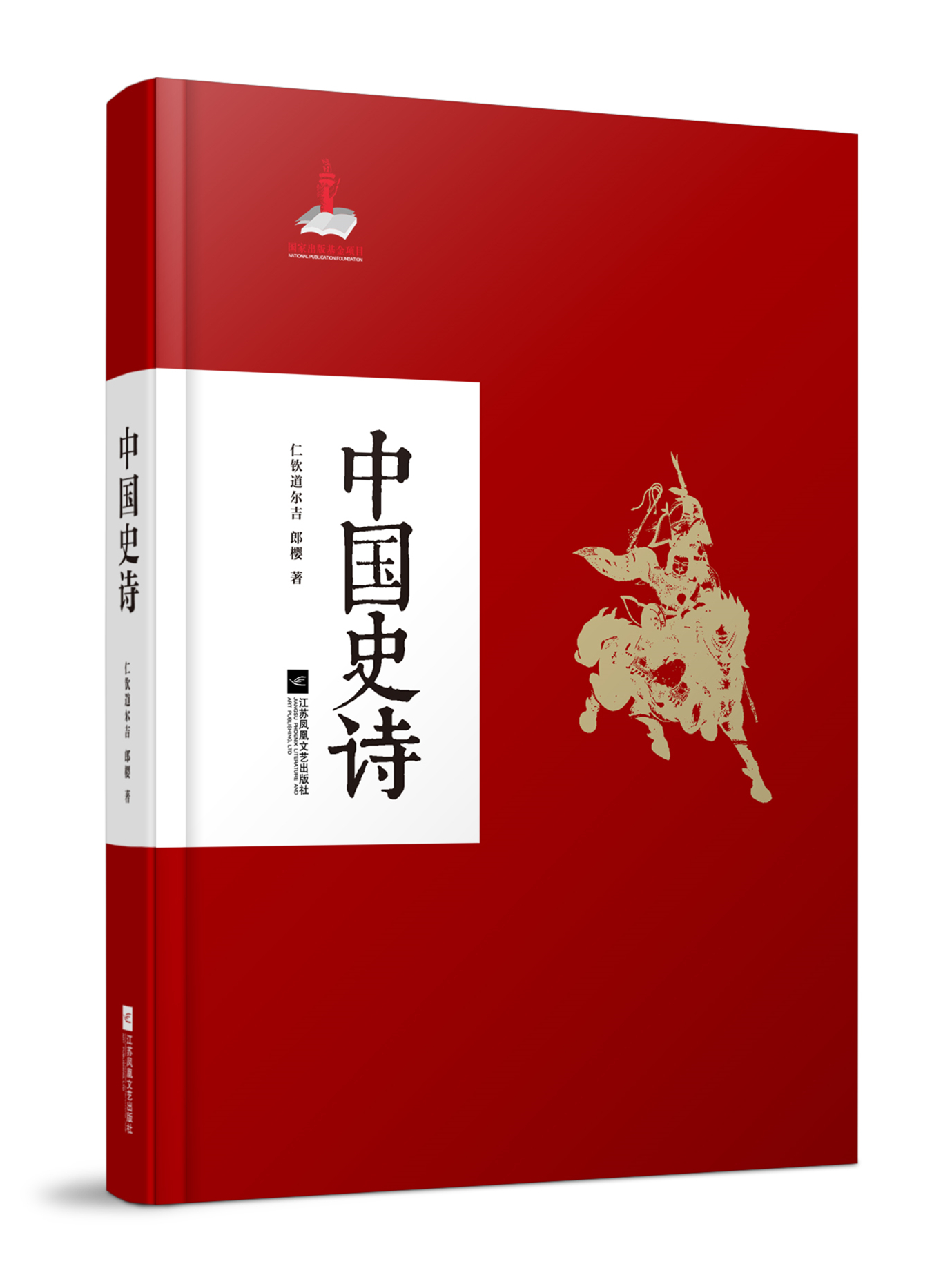
中国史诗(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学术专着)
《中国史诗》立足于我国丰富的史诗资源,在对我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及南方原始性史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进行了综合梳理与比较研究,对它们的发生髮展规律、叙事方式、结构类型、人物形象、艺人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中国史诗》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权威学者,其注重史诗形成、发展规律的探讨,加强对于国外史诗理论的翻译和译介,尽力做到以史诗的形成与发展为脉络,加强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及南方英雄史诗群的研究,并对我国史诗的发展规律进行一些探讨。
本书入选“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基本介绍
- 书名:中国史诗
- 作者:仁钦道尔吉、郎樱
- ISBN:978-7-5399-8832-0
- 类别:文化/史诗研究
- 页数:604
- 定价:180
-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 装帧:精装
- 开本:718*1000mm 1/16
内容简介
《中国史诗》是一部由社科院着名学者郎樱、仁钦道尔吉共同编写完成的、反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史诗文学艺术形式的缘起、形态、样式、规律、发展和唱演历史及对此梳理记录的一部完备、全面的专着。书稿吸收了数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中国民间及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繁荣新时期文学研究,促进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厚重的着作,不管是在中国史诗的观念表达上,还是在中国史诗的存在样态描述上,都堪称中国史诗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作者简介
仁钦道尔吉,男,1936年2月26日生,蒙古族,内蒙古巴林右旗人。1960年毕业于蒙古国立乔巴山大学蒙古语文历史系。中国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蒙古学协会秘书长。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从事蒙古族史诗,着述颇丰。
郎樱,女,1941年4月出生,籍贯北京。二级研究员、博士导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主要学术专长是维吾尔及突厥民族文学,长期从事柯尔克孜民族史诗《玛纳斯》研究。
出版背景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一部史诗,尤其是一部宏大的民族史诗,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史诗流传于少数民族地区,蕴藏量相当丰厚,举世闻名的三大英雄史诗——藏蒙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每部都在20多万诗行以上,规模宏伟,气势磅礴,至今仍在口耳相传,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除三大史诗之外,还有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及南方各民族史诗,总计约有500多部。
世界上的史诗绝大多数是书面史诗,而我国的史诗,至今仍在民众中口耳相传,是“活形态”史诗。其中,有许多内容极为古老,有创世史诗、狩猎史诗,英雄史诗等。因此,对于这种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史诗研究成为一项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目前,国内对于史诗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是,尚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史诗的着作问世。 由仁钦道尔吉与郎樱二人历经多年撰写的《中国史诗》,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进行综合性与比较研究,注重史诗形成、发展规律的探讨,加强对于国外史诗理论的翻译、译介,填补了此领域的学术空白。该着作资料翔实,内容全面,论析深刻。其出版成果,必然在弘扬、宣传、普及中国史诗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该着作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现实意义。
图书特色
★完备细述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生成、发展以及现状之专着,填补国内空白;
★全面展示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学的杰出成就,犹如徐徐展开一幅史诗画卷;
★细緻描绘史诗人物形象、性格及场景设定,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指引与参考;
★吸收数十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成果,代表国内学术界史诗研究至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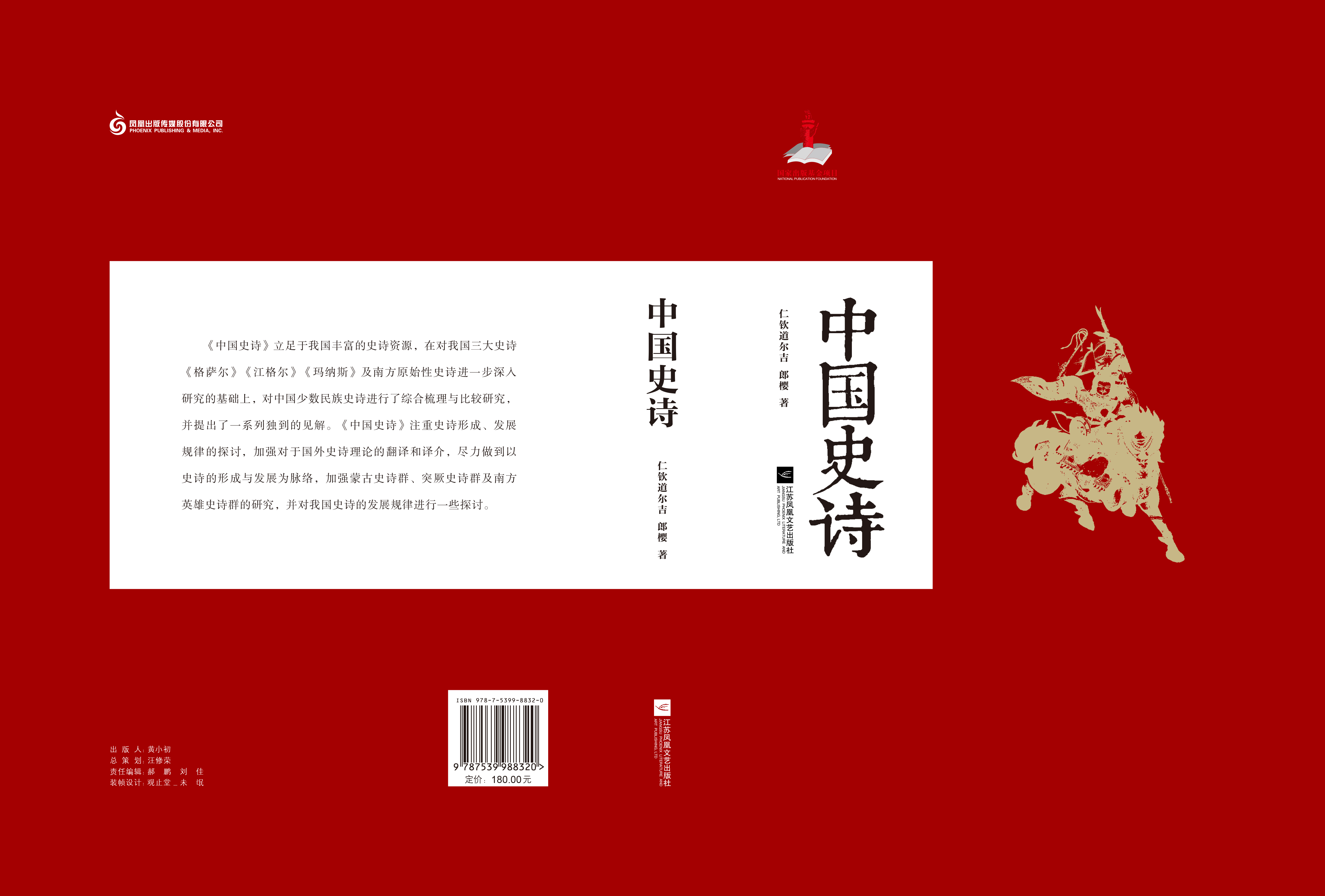
作品目录
绪论
第一编 早期史诗
第一章 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章 南方民族创世史诗
第三章 抢婚型英雄史诗
第四章 考验婚型英雄史诗
第五章 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型英雄史诗
第六章 勇士与独眼巨人、地下妖孽斗争型英雄史诗
第二编 中小型英雄史诗
第一章 蒙古英雄史诗的特徵
第二章 蒙古英雄史诗人物和情节的发展
第三章 婚事加征战型英雄史诗
第四章 两次征战型英雄史诗
第五章 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
第六章 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形成
第七章 狩猎型突厥英雄
第八章 古老的突厥英雄史诗
第九章 突厥英雄史诗的部落特徵
第十章 克普恰克部落突厥英雄史诗
第十一章 乌古斯部落突厥英雄史诗
第十二章 晚期突厥部落英雄史诗
第十三章 早期南方英雄史诗
第十四章 壮族与侗族英雄史诗
第十五章 彝族英雄史诗
第十六章 傣族英雄史诗
第十七章 苗族英雄《亚鲁王》
第三编 长篇英雄史诗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 三大英雄史诗概述
第二章 藏族史诗《格萨尔》
第三章 《格萨尔》的传承
第四章 蒙古《格斯尔》的独特性
第五章 蒙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传承
第六章 《江格尔》的形成和故事梗概
第七章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
第八章 《玛纳斯》的传承
摘要
绪论 第一节 史诗的表达与族群的认同
随着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东渐,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传入我国。“史诗”一词的英语epic直接来源于希腊语的epkos和拉丁语的epikos, 从词源上讲则与古希腊语的epos相关。该词的原意为话、话语,后来引申为初期的口传叙事诗,或口头吟诵的史诗片段。史诗这一概念传入我国当在19世纪末期。在18世纪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的着作《论史诗》中指出,“史诗”一辞彙来自希腊文,原意为“说话”。只是由于习惯相沿,这个词才与用诗体写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叙事的叙事联繫起来。目前,关于史诗的概念,常被指描写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大量歌颂英雄丰功伟绩的传说以书面或是口头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在西方,史诗主要指《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叙述英雄传奇经历和事迹的英雄史诗。关于史诗的定义,《维基百科》史诗条目写道:“史诗是一种以长篇叙事为体裁讲述英雄人物(来源于历史或是神话中)的经历或是事迹的诗。”我国的《大百科全书》史诗条目是这样说的:“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通常指以传说或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古代民间长篇叙事诗。史诗主要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害,抵御外侮的斗争及其英雄事迹。”
我国是一个史诗蕴藏量极为丰富的国家,约有各类史诗数百部之多,它们分布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地区,除知识分子用“史诗”( Epos )一词之外,人民民众对“Epos ”一词并不认同。其实,每个民族对史诗都有自己传统的称谓,如柯尔克孜人民称史诗为“交毛克”(joomok故事), 维吾尔人民称史诗作“达斯坦”(dastan叙事诗),哈萨克民众称史诗为“吉尔”为(jer古歌),蒙古族人民称史诗为“陶兀勒”(tuul故事), 藏族人民称史诗为“仲”(sgrun广义为故事,狭义指《格萨尔》),侗族民众称史诗为“嘎公古”(gagonggu 古老歌),四川彝族称史诗为“穆莫哈玛”(mupmop hxamat 口头传颂的诗歌),韵文体史诗称作“勒俄”(hnewo),壮族称史诗作“四幺”(saw mo师公诵唱的史诗),湘西苗族称史诗作“杜奥特”(dut ghot意为古老诵词),朝鲜族人民则称史诗为“苏萨什”(susa shi)等等。
中国本土史诗传统与西方史诗传统不尽相同。因而,我国对史诗的定义和範畴的界定,也有异于西方的“史诗”(Epos )的界定,其含义及所指也是有同有异。西方的史诗,以希腊史诗为辉煌的“典型”,强调史诗一定要有战争,一定要描写英雄传奇与英雄事迹。其实,这一西方的史诗概念,并不能涵盖我国南方与北方民族的史诗传统。例如,我国南方各民族中传承着大量的创世史诗,以及塑造文化英雄为主的英雄史诗。南方民族是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活态”史诗,是无法用西方的史诗定义所概括的。在早期的突厥—蒙古史诗中,也有许多史诗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例如,至今在柯尔克孜民众中口头传承的《考交加什》,描写的神箭手考交加什因触怒母野山羊神而受到报应,被母野山羊神施魔法被定在悬崖边冻饿而死的故事。类似活态的、具有浓郁神话色彩史诗,在我国南方与北方民族中均大量存在。因此,如果以希腊史诗为典範的、强调描写英雄传奇与英雄事迹的史诗概念,来附会我国丰富多彩的史诗的话,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只会模糊我们的视界,使中国史诗类型的丰富性贫乏化”1钟敬文先生认为,“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的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记述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一部形象化的历史。”1,这是首次明确将我国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民族迁徙史诗以及北方民族英雄史诗包括在内的、结合中国史诗实际的史诗定义。
儘管史诗与叙事诗的概念难以严格区分,但是,在我国,“叙事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类,因此,我国的史诗研究者还是努力将二者加以区分。叙事诗可以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而史诗往往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尚无能力征服自然的时代,不可能产生史诗。那时,极需解决的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社会开始从野蛮时期迈入文明的门坎。这时,包括氏族、部落、族群在内的群体意识觉醒。
是关注群体的命运,还是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与爱情历经,这是我国区分史诗与叙事诗的重要标尺。无论是大型史诗,或是小型史诗,所关注的都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的事业与命运。史诗注重群体的意识,群体的观念,群体的荣誉,群体的利益。也就是说,族群的事业与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
史诗的叙事与一般的叙事诗的叙事,迥然有异。史诗的叙事庄严、神圣、宏伟。史诗的这种庄严性、神圣性与宏伟性,既体现在口头文本之中,更体现在史诗的演述中。史诗对于人与事的叙述,採取“全能叙事视角”,即史诗叙述者洞晓史诗中所有人物与事件的来龙去脉,既知道它们的过去,又知道它们的未来。史诗的时空观无限广阔,发生在天界、人间与地下界之事,甚至发生在遥远古代以及跨越漫长时代的一切事物,也都在史诗叙述者的视角之内。
与一般的叙事诗相比较,史诗所包容的文化信息量要大得多,史诗的内容古老,文化底蕴丰厚。史诗在继承族群口头传统的基础上,历经漫长的口头传承过程,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及谚语等。口头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宝库,是一座展示民族精神的博物馆,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一部史诗,尤其是一部宏大的民族史诗,内容丰富,气势恢宏,在民族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史诗”,主要指希腊史诗类的英雄史诗。而我国的史诗,既有规模宏伟的三大英雄史诗,也有浓郁神话色彩与充满神奇幻想的狩猎史诗和古老的英雄史诗,还有创世史诗、迁徙史诗等。西方的史诗,虽然具有口头史诗程式化的特点,但是,目前西方的经典史诗基本上已经书面化了,成为书面史诗,目前在民众中已鲜有口传。然而,我国绝大多数的史诗仍然是“活态”史诗,仍以口头形式传承着,这是我国史诗突出的特点。因此,史诗演述的语境,史诗演述与仪式,史诗的表达认同等重要内容的涵盖,使中国史诗的概念与西方史诗的概念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实,关于史诗的定义,国外一些学者也从新的视角提出新的命题。芬兰着名学者劳里·航柯认为:“(说)史诗是‘一种风格高雅的长篇口头诗歌,详细叙述了一个传统中或历史上的英雄的业绩’, 这种陈腐解释带来的问题是,与它发生关係的总是特殊的英雄史诗,以至忽视了相当多的传统史诗种类。近些年中,西方学者倍感“荷马样板”是束缚,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源头活水。在史诗的比较研究中这种态度更为突出,其中包括那些非欧洲口头史诗的研究着作,这些是建立在活态传统调查经验之上的成果。对此,约翰·威连慕·约森讲过多次,他说:我希望希腊史诗刻板的模式,一种在现实行为里再也看不到的僵死的传统,不该继续统治学者的思想。希腊传统只是许多传统之一。在非洲和其他许多地区,人们可以在自然语境中去观察活态史诗传统。在表演和养育史诗的许多地区,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史诗是关于範例的伟大叙事,作为超故事是被专门的歌手最初表演的,它在篇幅长度、表现力与内容的重要性上超过其他的叙事,在传统社会或接受史诗的群体中具有认同表达源泉的功能。对外来的耳朵来说这种沉长无味的、重複的叙事,都在特殊群体成员的记忆中通过他们对史诗特徵和事件的认同达到崇高辉煌。对史诗的接受也是它存在的基本因素。如果没有某些群体至少是一部分的欣赏和热情,一个叙事便不能轻易地被划为史诗。”劳里·航柯所提出的史诗定义,适用于欧洲以外的“活态史诗”传统。“活态”史诗表达认同的文化功能更为突出,表现出更多的激情与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学者对史诗定义的论述,视角也发生着转变。例如,有的学者从文类视角论述史诗:“中国史诗文类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定义:(一)形式方面,以韵文或是韵散交杂来记述长篇叙事可以口头传唱的诗歌;(二)时间方面,它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后期;(三)内容方面,可分为‘创世史诗’与‘英雄史诗’”。 而有的学者,则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论述史诗的定义:“什幺是史诗呢?一般文学教科书给出的定义实在是差强人意的。藉助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我们终于了解了史诗及其产生奥秘。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都在远古时留下故事与歌谣。在某些文化中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并成为经典性的世代传唱作品的,正是史诗。”
综上所述,史诗这一学术用语,与神话、话剧等外来术语一样,已被我国学术界所接受,并成为我们文艺文类的重要用语。“史诗”一词从西方进入我国,结合我国的史诗的实际与中国史诗传统,中国史诗的定义以及所涵盖的史诗类型,已与西方的史诗理念不尽相同。
在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史诗,既有共性,也同样存在差异。例如,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与北方民族英雄史诗之间,也存在差异。即使同是南方民族,由于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语系语族、地域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不同民族的史诗传统、史诗传承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同与异,构成了我国史诗的丰富性。正如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史诗的价值不是历史的,而是文化的,每一个民族的史诗都有其特殊性。以往研究史诗,主要受西洋理论的影响,以希腊史诗为‘典型’。”为扭转此种状况,应以中国本土史诗传统为主,借鉴国外史诗研究理论,推动中国史诗理论建设。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
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